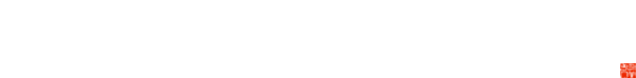【作者简介】陈蕴茜,威尼斯9499登录入口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3 陈蕴茜(1965—),女,江苏省南京市人,威尼斯9499登录入口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威尼斯9499登录入口人文社科高级研究院兼职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史研究。
近代民族国家出现后,共同的社会记忆是国家与社会运作的重要合法性来源,因此,作为人们对过去事件、人物表达崇敬、景仰和怀念行为的纪念空间日益受到重视,因为纪念空间具有调动情感、引发思考、唤起并塑造记忆的功能,与社会记忆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但是,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之间不是不证自明的关系,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纪念空间得以存在并发挥塑造社会记忆功能的基础,而且在近代中国,纪念空间的转换与社会记忆的塑造更具有现代性与本土性,这是研究中国记忆不可忽略的关键。
一、纪念空间的分类及构成
纪念空间有多种分类方法。从社会学的角度分类,可以分为个人与社会两大类。个人纪念空间主要是与家族、地缘、血缘相关联的纪念空间,如祠堂、墓地、家庙等。而公共纪念空间,则包括由国家统一修建或由社会捐助修建的纪念场所,用于公共纪念活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与渗透较弱,国家无力在地方修建大量公共设施,除孔庙等外,多数纪念空间属于个人性的或社区性的。但是,近代以后,情况发生变化,公共纪念空间随着国家力量的强大而迅速扩展。
纪念空间一般由纪念物及历史环境所构成。纪念物是人类的创造物。1903年,奥地利艺术史家李格尔(Alois Riegl,1858—1905)在《纪念碑的现代崇拜:它的性质和起源》一文中,根据意义属性将纪念物分为五种类型:“丧葬纪念物”(sepulchral monuments)、“象征永久性帝国威权的纪念物”(prominent symbols of imperial authority)、“政治地位纪念物”(political status)、“象征国家或区域认同的纪念物”(identities nation region)、“具威信符号的纪念物”(prestigious signature)。这一分类基本上涵盖了公共纪念物的特性,同时兼顾到了国家与地方、政治与社会等不同属性纪念物的价值。而根据建造的原初目的,李格尔又将纪念物分为“意图性纪念物(intentional monument)”与“非意图性纪念物(unintentional monument)”,而非意图性纪念物也可将之归类为“历史性纪念物”的一部分,并且以其“纪念性价值”(commemorative value)来区分,即“非意图性纪念物”在最初建立时并无使之成为纪念物的原始意图;而“意图性纪念物”则是依其当初预设的、或制作人试图表达的纪念性意图为出发点。①
按照李格尔对纪念物的分类法,纪念空间其实也可以划分为非意图性纪念空间与意图性纪念空间。前者如革命遗址遗迹,包括一般性墓地、战场遗址、革命活动旧址、故居等;后者则包括公墓、忠烈祠、纪念碑、纪念馆、博物馆、纪念堂、纪念亭、塑像等。但是,这种分类并不是绝对的,如名人故居、墓地等最初为非意图纪念空间,但随着历史的变迁,人们为了表达对主人的纪念,往往会在故居或墓地建立附属建筑或设置历史陈列,这样非意图性纪念空间也会向意图性纪念空间转化。
建筑是纪念空间的基础元素,古往今来,纪念性建筑在城市空间中都扮演着超越时空、表达永恒价值的角色,但广场、道路、行政区划等非建筑形态的纪念空间也具有纪念价值。我们可以借用涂尔干对“神圣/世俗”世界的两分法,来将它们做一分类。如忠烈祠、中山陵等就是典型的神圣空间,而公园、道路等则属于世俗世界的纪念空间。分类法的综合运用,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深入地解读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的关系。
无论如何划分,纪念空间都具有其基本特质——空间性。意图性纪念空间会“通过建筑、雕塑、碑、柱、门、墙等元素来进行空间的限定和形象的塑造”。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则“运用隐喻、暗示、联想等环境手段来引导人们的思考,启发人们的想象力,从而表达出空间的纪念性”。②但非意图性纪念空间也会通过附属性建筑、内部空间布局、标志导引等来加以衬托,以此突出其纪念性。
纪念空间的功能是创造历史(英雄和历史事件)的永恒价值,这需要通过物质性的营造和空间策略的运用来建构。在意图性纪念空间中,这一特性表现尤为突出。首先,运用长长的轴线做对称式布局来彰显被纪念者的中心定位。其次,在外观造型上,设计者常常会以几何形体及简单的组合形式来衬托纪念空间的雄壮和稳固。再次,采用坚硬的花岗岩、青石等石料或青铜等坚固永久性材料,以象征纪念对象的精神永存。最后,纪念空间多栽种苍松翠柏等常青植物,以象征被纪念的精神如树木般常青,生生不息。③
二、纪念空间与记忆生成
纪念空间最重要的特性是纪念性。所谓纪念性,是“由人们为了其外在需求而拥有可显现其内在生命、其行动、社会性概念象征/符号所延伸而来的”。因为纪念物在拉丁文中最初的含义是“可被提醒的东西”,是能被传递给往后几个世代的东西,就是某种象征/符号。④可见,纪念空间的内容是历史,其指向则是唤起记忆。
对空间与记忆关系的重视,从古至今皆而有之。公元前500年,古希腊诗人西莫尼底斯(Simonides)利用建筑中的空间布置,建构人为的记忆。⑤当代法国著名社会记忆研究专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主编了多卷本的《重新思考法国——记忆之场》(Rethinking France:Lieux de mémoire),其中大量探讨纪念空间(宫殿、咖啡馆、雕塑、教堂)作为“记忆之场”在民族与国家建构中的作用。
诺拉等特别探讨了纪念性空间所具有的双重功能:一是回溯性功能,即让人们回溯历史,唤起人们的记忆,特别是非意图性纪念空间向意图性纪念空间转换之后,这种功能更为明显;二是前瞻性功能,即通过纪念空间的营造,将历史事件与未来发展进行了勾连,让人们通过参观纪念空间而获得历史认同,从而确定未来发展。其实,这种双重功能既包含个人化的纪念空间,也涵盖集体性的纪念空间。但是,诺拉等更强调公共性的纪念场所作为“记忆的介质”(milieux de mémoire)对社会记忆的影响。⑥
纪念空间具有塑造记忆的功能,而社会记忆又是民族或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可以为统治者提供合法性来源。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近代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建立,就是因为人们拥有共享的记忆,而提供这些记忆资源的载体之一就是纪念空间,如国家设立的纪念碑、纪念馆、博物馆等场所。⑦这些纪念空间以不同的形式叙述着民族的历史或者革命的历史,成为全民共享、保存、展示记忆的装置,为民族和国家提供认同的资源。
纵观人类发展史,特别是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以来,世界各国都普遍建立国家性纪念空间,以服务于强化民族或国家记忆、满足统治合法化的需求。也由于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之间的密切关系,执政者或外来入侵者有意毁灭纪念空间,以达到歪曲或抹煞记忆的目的。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规模摧毁波兰首都华沙的传统建筑,对王宫以及作为华沙城市象征的美人鱼广场狂轰滥炸,其目的是摧毁波兰人的民族集体记忆。而战后,波兰人在百废待兴之时,花巨资按战前原样复建华沙古城,其目的则是恢复纪念空间,从而重塑民族自信心。
当然,纪念空间对社会记忆的塑造,也并不是完全按照国家的预设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如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建造中山陵的目的,是让人们对国民党的精神领袖孙中山形成深刻的记忆,进而形成党国认同。然而,社会各界对中山陵的认识却是多义的:有的利用中山陵来表达对蒋介石不抵抗日本政策的不满;有的则利用中山陵来宣泄自己对个人政治待遇不公的愤懑;而对普通民众而言,中山陵有时只是消费文化中的旅游景观。因此,在记忆的塑造过程中,纪念空间能否对记忆发挥建造者预设的功能不是不言自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念空间不是简单的物质化或精神化的空间,而是一个多种权力、资本争夺的场域。因为,就本质而言,那不是在争夺空间,而是在争夺记忆,争夺赖以统治、维系群体的政治遗产与合法性。
三、记忆主体对纪念空间的重塑
受诺拉记忆理论的影响,学界更多的是关注纪念空间对社会记忆的影响,而事实上,纪念空间虽然可以塑造人们的记忆,但记忆的主体并不是被动的受塑造者,记忆与空间也不是单向的决定关系,而是双向的互动关系——记忆可以强化空间的纪念性,可以唤起被遗忘的空间。换言之,记忆可以重塑空间。
一方面,记忆的形成与纪念空间的关系是建立在记忆主体熟悉被纪念者或对事件具有体验,或对被纪念者、事件具有相关知识积累。当一个人具有事件体验,而这种体验与被纪念者关系一致时,则事件体验与纪念空间是正向关系,这种记忆可以起到强化纪念空间属性的作用;但如果事件体验者与纪念空间建设者呈反向关系,则他们不会认同纪念空间,甚至会通过漠视、批判或抗议等形式来消解纪念空间。另一方面,作为非事件体验者,只能通过代际传递、纪念空间设置者的宣传,对被纪念者或事件形成扬•阿斯曼(Jan Assmann)所说的“文化记忆”,即达成一种沟通记忆,从而使事件体验者的个体记忆变成集体记忆。⑧纪念空间不是唯一性社会记忆载体,它往往与历史事件的文本叙述相关联。这样,就需要记忆主体对纪念空间有亲历或知识体验。当人们进入空间时,记忆才会被唤起,否则纪念空间唤起记忆的功能是有限的。
记忆对空间的重塑体现在纪念仪式的举行可以强化空间的纪念性。虽然纪念空间是纪念仪式举行的基础,它可以为仪式提供场所精神的支撑,营造纪念仪式的神圣氛围与历史现场感,让人们更易与历史产生关联感,在仪式实践中形成深刻的记忆。但是,纪念空间因为有了纪念仪式,其所具有的纪念性才被突出并抽离出来,通过仪式而被赋予神圣性。因此,纪念仪式反过来强化了空间的纪念性。否则,纪念空间就是僵死的、没有生命力的空间,也难以对人们的记忆产生影响。而纪念仪式的举行,则有赖于记忆主体的参与。
但也必须强调,记忆的形成既来自空间,也来自非纪念空间的影响,学者不能忽略纪念空间在特定时代因过度的宣传而具有强力塑造记忆的功能。许多纪念空间的功能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淡化,但它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对社会记忆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不能以今天简单的经验来加以推翻。
记忆主体对纪念空间的影响还体现在纪念空间的建设必须考虑被纪念者遗属的记忆。一般而言,历史事件纪念碑大多属于公共纪念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抹煞个人记忆,有些纪念碑在维护公共记忆的基础上兼顾个人记忆。例如,美国越战纪念碑刻上了战死者的名字,并且在墙边保留了大量私人物品,包括照片、信件、玩具熊、勋章、衣物等,它成为个体记忆与公共记忆有机融合的载体。又如,中国台北“二二八”纪念公园在选址方面,委员会考虑了受难者遗属的要求,而且为了考虑受难者家属能够接受,而将原来评审的“二二八”纪念碑第二方案替代了第一方案。⑨这样,这个纪念碑就具有集体记忆包容个体记忆的意义,个体记忆在纪念空间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记忆主体还具有唤起纪念空间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记忆常常被纪念空间唤起,但有时却是记忆“唤起”了空间。纪念空间的兴建并不一定是必然的,如果没有社会记忆的建构,可能空间的纪念性也会被遗忘。拉贝故居位于威尼斯9499登录入口,多年来一直作为职工宿舍而被人们遗忘了。但是,随着南京大屠杀记忆成为全民族最重要的创伤记忆,有关大屠杀的纪念空间被记忆唤起。拉贝故居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变成纪念馆,成为那段创伤记忆的又一载体,深刻的创伤记忆唤起了已被遗忘的纪念空间。当然,这一纪念空间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创伤记忆。
总之,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是一组互构关系。纪念空间在完成一系列建构性元素的排列后,即能发挥塑造记忆的作用。但中国学者在研究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的关系时,其一,不能忽略记忆主体对纪念空间的影响。因为,纪念空间既可以塑造社会记忆,也受社会记忆的影响。其二,不能忽略本土性。原因在于,一方面,虽然中国众多的公共纪念空间是随着近代西方势力与文化进入中国的,但无论是其建筑特征还是纪念属性以及仪式对空间的再塑造,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本土性;另一方面,虽然公共纪念空间多为政府设置,具有公共空间的现代性特征,但民间仪式如烧纸钱等大量出现于公共纪念空间,使这些空间体现出本土性。由此,记忆不是单纯被塑造与改造的对象,它可以改变纪念空间的属性,并增加其象征意义。随着学者关注社会个体而不仅仅是“大而空”的社会,个体记忆与集体社会之间的互构关系也被纳入研究范畴。纪念空间的建设也开始关注个体记忆的元素。纪念空间形塑记忆不是自然而然的,而必须将记忆主体也纳入记忆建构体系之中,多维度进行强化,才能真正发挥纪念空间的作用。对社会记忆的研究,有助于厘清被遗忘的纪念空间,起到唤起与重塑空间的作用,从而让纪念空间更好地发挥强化社会记忆、促进认同的功能。
注释:
①A. Riegl,The Modern Cult of Monuments:Its Character and Its Origin(1903),Oppositions,1982,Vol.25.pp.31—35,转引自林蕙玟、傅朝卿:《战争纪念性意义之差异性研究——以金门与美国盖兹堡之役纪念物之设置意涵为探讨》,《建筑学报》,第62期,2007年12月。
②田云庆编著:《室外环境设计基础》,第96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③刘禹:《纪念性空间的研究》,第13页,北京林业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硕士论文,2006。
④S. Giedion,The Need for a New Monumentality,转引自林蕙玟、傅朝卿:《战争纪念性意义之差异性研究——以金门与美国盖兹堡之役纪念物之设置意涵为探讨》。
⑤[美]索尔索:《认知心理学》,第283页,黄希庭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
⑥Hue-Tam Ho Tai, Pierre Nora and France National Mem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6. No. 3.(Jun., 2001), pp. 906—922.
⑦[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⑧Jan Assmann, Collective Memory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Jan Assmann and John Czaplicka, Cultural History/Cultural Studies, New German Critique, No. 65, Spring-Summer, 1995. pp. 125—133.
⑨胡蕙玟、傅朝卿:《纪念场域、历史的重新书写与再现:二二八事件纪念物设置于台湾都市空间所呈现的历史新意义》,载《建筑学报》,第66期,2008年12月。
《学术月刊》(沪)2012年7期第134~137页
作者陈蕴茜,系南大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大人文社科高级研究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