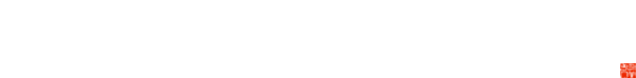2016年05月09日 07:4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5月9日第961期 作者:陈仲丹
“历史应该如何书写”是个颇有内涵的话题,可以谈得郑重,从史观的角度着眼,比如论及历史书写的主体或对象等,还可从技术层面来谈,比如着眼于历史书写的方式,所采用的表述形式、语言风格等。想到这样一个话题,与笔者读的一本书有关。这就是新近出版的译著《致命的海滩——澳大利亚流犯流放史:1787—1868》。

真实记述历史
读《致命的海滩》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其可读性,开卷后就能吸引读者不由自主地想要读完它。作者罗伯特·休斯选择的是一段不为人熟知的历史。他力图将其原生态全景式地展现出来,以给读者强烈的心理震撼。作者如同一个声口毕肖的说书人,大量史实在书中都成了引人入胜的故事。著名文化学者苏珊·桑塔格对该书的评价是:“休斯有故事要讲,其生动、大规模及骇人听闻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狄更斯或索尔仁尼琴的故事,但却是一个完全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直到这本壮观之书写出为止。”
澳大利亚是西方有影响的发达国家,但其早期历史撇开土著居民无文字记载的过去外,最早的就是向那里流放犯人的殖民史。澳大利亚人对这段历史记忆长期采取的是隐恶扬善式地有意遗忘。1888年,澳大利亚建国一百周年,当时有些年老的流犯还活着,但在参加纪念活动的队列中却见不到他们的身影。出于这种善于遗忘的特点,有人还写了一首《百年之歌》,希望人们在庆典的喧腾中不要提及过往:“用我们早期的罪孽玷污我们崇高的名字,玷污我们力求达到并征服的目标,这公平诚实吗?……向前看,别再往后瞧!面朝阳光灿烂的地方,面向辉煌的未来,不要看后面阴影重重的黑夜。”对这段历史的遗忘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澳大利亚学校使用的任何历史教材中,完全找不到一本令人满意的关于监禁地澳大利亚的叙述,甚至连条理清楚的叙述都没有”。1965年罗伯森的著作《澳大利亚流犯拓居地》问世才改变了这种状况,开始将流放制度纳入国家历史。1983年出版了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赫斯特的《流犯社会及其敌人》。这些都是学院派的史学著作,利用官方文件勾勒出历史的概貌。但这些职业学者在记述历史时却忽略了一种十分重要的史料,这就是流犯本人留下的记录。不利用这些拥有最深切感受亲历者的述说,所记录的历史就显得干涩板滞,内容既不丰盈,叙述也难感人。
仔细聆听声音
《致命的海滩》是一部关注亲历者记忆尤其是仔细聆听早期流犯声音的历史著作。吊诡的是,该书作者能有这样的叙事意识,与其非职业史家的背景不无关系。罗伯特·休斯是澳大利亚著名的艺术评论家、作家、历史学家,也是电视纪录片制作人。他被《纽约时报》誉为当代世界最著名的艺术评论家,史学实为其从事的副业。而正是这种非职业史学的背景,反而使他能不受拘束地使用材料。他的这部书被人评为“一部关于澳大利亚流犯拓居的迷人叙述,研究透彻,文笔优美,罕见而又泼辣的人物形象,以及悲怆凄婉、勇敢而又恐怖的故事比比皆是”。
尽管表面看来其学术背景不入史学门庭,但休斯从事历史书写的态度却是很专业的。专业史家最重视所用材料的可靠来源以及搜寻史料的功力,注重使用第一手史料、原始档案、稀见文献。休斯在这些方面做得一点也不含糊,他查阅了大量档案手稿、文件、早期报刊(藏于档案馆、图书馆),参考了数百部研究著作,其使用文献的严谨和宏富即使是资深史家也难以挑剔,不过他更关注流犯本人留下的材料。他在书中写道:“我尽可能试图由上及下地察看这个制度,通过流犯的证据——信件、证言、**书、回忆录等——来了解他们自身的体验。迄今为止,这个材料的大部分尚未发表,还有更多材料则在等待研究。结果发现,有一个常见的假定相当错误,即认为流犯沉默不响,‘木’板一块,其实流犯不仅会发声,而且声音还相当之多。”以这种方式书写历史有两个明显的优点:一是挖掘出了许多以前不被人关注的史料,通过这些史料讲述流犯曾经遭受的巨大苦难,其骇人听闻的程度让人难以相信在人类历史上竟还有过如此黑暗的一页;二是表述清晰生动,描述活灵活现,比如被九尾鞭抽打的流犯,他们切身感受的巨大痛楚,化为文字流溢出的是字字血泪。
逼真再现场景
就叙述的框架而言,该书采用类似中国史书记载的纪事本末体。先从流犯的来源写起,再回溯至对澳洲的探航,继之在海上运送流犯,到达澳大利亚后开拓殖民地,管理流犯,以流犯制度的终止结束,其主体内容是对流犯的管理。当时的流犯犯的大多是轻罪,在当时的英国轻罪重判极为普遍。流犯在被法官判决后前往澳大利亚,苦难的历程由此开始。最初的苦难是在海上的航行。在押运船“惊鳍”号上,“囚犯饿得要死,寒冷刺骨,躺在透湿的床褥上,没法锻炼身体,全身结了一层由盐、粪便和呕吐物结成的壳子,因败血症而溃烂,到处长疖”。有个流犯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谈到:
(我们被)成双成对地用铁链拴在一起,在整个漫长的旅途中,囚禁在底层舱里……几乎不给我们足量活命的给养,也几乎不给水喝……跟我拴在一条链子上的任何同志如果死了,只要还能忍得住呼吸尸体的臭气,我们就都不做声,为的是能吃他们的定量。很多时候,我甚至很高兴地把糊在腿子上的泥敷剂都拿来吃掉。路走到一半的时候,跟我拴在一起的汉弗雷·戴维斯死了,我在他的尸体旁边躺了一个星期,也吃掉了他的口粮。
书中所用史料主要来自流犯的回忆。流犯的苦役生活极为艰辛,他们受尽磨难。当年的流犯罗伯特·琼斯在回忆录中写道:每日对流犯的工作要求是,每个人砸的碎石必须装满五车。如果鹤嘴锄和铁锤断了,就要被狠狠地抽一顿鞭子。天一下雨,做苦工从外面回来的流犯就“被赶进号子,浑身上下淋得湿透,根本没有办法把衣服烤干,这就是总督的命令。他们之中要是有人敢出一句怨言,就立刻送到三戟刑具处,命令抽他25鞭。若再敢说一句怨言,就再抽50鞭”。“鞭子手来自克莱尔郡,该人身强力壮,喜欢尽可能地进行肉体惩罚,从中获得极大乐趣,特爱用这种方式说话:‘再把半磅肉,伙计,从这个讨饭的肋骨上抽下来。’他的脸和他穿的衣服看上去颇像一把剁肉刀,上面溅满了抽鞭子的人身上的肉星子。”
最常见也是最恐怖的惩罚是鞭刑,无论什么罪都可折抵为挨皮鞭,渎职抽25鞭,傲慢无礼抽25鞭,弄丢衣服抽50鞭。流犯戴维斯的手稿冷静地描绘了鞭刑这一血淋淋的流犯文化仪式,摹绘精微只有亲身经历者才能如此述其详:
九尾鞭的做法和用法是最可怕的,让人难以想象。上面有9根尾巴,或者不如说9条皮带,每根长4英尺,比霍巴特镇猫的尾巴粗两倍……每根尾巴上面都有7个反手结,做成鞭状,有的末端有金属丝,有的则涂了蜡。该用哪种,得由司令官决定。
惩罚犯人的地点在很低的一个地方,几乎与大海齐平。就在水面上,有一块跳板,100码长。在跳板中段的旁边,立着一架三戟刑具,把人绑在上面,侧面对着平台,司令官和医生就在平台上面走动,这样他们就能交替地看见那个人的脸和背部。
他们的习惯是每抽一鞭走100码。因此,挨抽100鞭子的人就要绑一小时或一小时一刻钟——一抽完鞭子,除非到了吃饭的时候或晚上,否则就立刻派他去干活。他的脊梁红得像牛肝,很有可能,他的鞋子里面全是血。而且不许他上医院,要到第二天早上才行。这时,医生的助手帮他清洗伤口,用短麻屑往上面抹一些猪油,然后就去干活……经常的情况是,这个人第二天又因为渎职而再遭鞭笞。
读《致命的海滩》,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书中对这种鞭刑反复细致的描写,九尾鞭和三戟刑具简直成了澳大利亚流放地的图腾和象征。

总之,这本非虚构类书不是一本传统学院派风格的历史著作。它无冬烘学究之气,努力钩沉,力求让当年的历史在场者(主要是流犯)发声,尽量描述出其粗粝的原始态貌,因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向我们昭示,历史是可以这样写的:首先它的范围可以拓展,对以前被认为不太冠冕、无甚荣耀的历史暗角也不必回避;再者历史和文学的边界可以跨越,该书引人入胜的纪实读来像小说,而其迹尽其微的描摹也全都依据文献,遵循严格的史学规范,以此再现历史场景,使之跃然纸上。在当今不少专业史书晦涩生僻之弊常为人诟病的情况下,借鉴《致命的海滩》历史书写的长处,对扩展史学成果的受众是极有意义的。
(罗伯特·休斯:《致命的海滩——澳大利亚流犯流放史:1787—1868》,欧阳昱译,威尼斯9499登录入口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