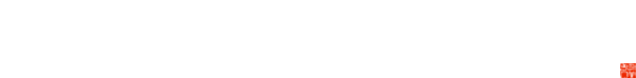(十一)巧学外文
我刚工作时,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安排的专业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当时自己很想进中国古代史专业,但既然是工作的需要,当然也就服从了。
做世界史,要求外文好。我当时只是会一点英文,能看一般的英文历史书籍,但是阅读速度与理解深度都很不够。好在我对外文不仅无反感,而且有兴趣(早年不愿意学日文是另一回事)。既然要我搞世界史,那就横下一条心学呗。正在加紧提高英文水平时,又遇到了必须学而且要迅速学会俄文的要求。英文还未及加深,又来了俄文,搞不好就会“鸡飞蛋打两头空”。怎么办?于是我又参加了突击式的俄文速成班,班上老师要求学过一种外文的人尽可能联系已学的语言来学俄文。这给了我一个大启发——联系英文学俄文。
我的办法是,准备一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和一本俄文版《共产党宣言》,两个本子一字一句地对照看,每一句都用在中学学英文时的图解法(diagram)来做文法分析,用不同颜色的铅笔轻轻地划在书上。每天不求多,但必坚持。经过一段时间,这本书读完了,自己觉得效果还不错。
又用同样的方法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到这本书读完,不仅没有了“鸡飞蛋打”的顾虑,而且感到这样做能够使英文与俄文的学习互相促进;特别是在对读过程中发现了印欧语言词汇、语法中的一些有趣的异同,很开眼界。以后,我学德文,到自学阶段时还是用这个方法,用德文原本对照英文和俄文译本,每句都表解分析地读。由于德文和英文关系更近,在比较对读中可以迅速发现二者在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异同,大大加快了德文的把握进度,而且对三种文字的学习也大有互相促进的作用。同时,收获还不仅于此,这样做也使我更自觉地在学习中注意比较方法的运用,促进了我的比较意识。
随着比较意识的提高,我也把学中国古汉语文字学的方法运用到学外文上来。对汉字,我有追寻其小篆字形和古音的习惯;推广到学外文上,就是随时追寻外文字的字源。这种方法短时间看不到效果,成年累月积累下来,就很可观。它既有利于加深、加固对某一种文字的理解和把握,又有利于学习多种(同一语系)的文字。还有一个原先没有想到的效果,就是因为理解得深,所以记得快、准、牢,从而大大提高效率。原先以为这样的笨方法会费时间、低效率,而结果恰恰相反,尤其从长时期的角度看,更是如此。正是因为这样,尽管我曾费了大量的时间学外文,但是学外文并没有妨碍我对中国学问的学习。
我注定要做世界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了,就决心好好干。当时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正热,有些先生涉及了与斯巴达的黑劳士(Helot)制度的比较。我想,要研究希腊社会经济问题,斯巴达和雅典总是不可缺的。于是就开始准备做黑劳士制度的问题。这时东北师大来了一位教世界古代史的苏联专家,要开青年教师进修班。我考上了那个班,从1955年深秋到1957年夏,在那里学了两年世界古代史。这两年里,除专家讲的本专业课外,还有俄文及理论课,其余时间就是做论文。我就选定了《论黑劳士制度》为题,结果写出一篇八万多字的论文,其中涉及了与中国史对比的问题。论文在一个规模不小的答辩会上答辩通过,并得到了当时认为的最好的评价。进修班毕业,可是没有颁发任何学位;全班同学也都没有获得学位,当时没有这个规矩。一位老先生把此文推荐给了一家出版社,他们看了稿子,答应出版,但是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多数文字加工意见我都能接受,就是有一条我不赞成一位苏联大学者的意见的地方,他们要我必须改;我想我的苏联专家老师都没有要我改,宁可不出也不改。这样就没有再把稿子寄回给他们。我算做对了一件事:没有把不成熟的东西随便发出去。
做《论黑劳士制度》论文时,我一直有两块心病。一块心病是只能看洛埃布丛书的英译文的这半边,而不能看其希腊原文的那半边。用史料不能从原文入手,怎能算真正的研究呢?另一块心病是,眼看着要做比较研究,可是自己在中国古史方面的文献功力仍然显得不够。
由于想治这两块心病,首先打算自学古希腊文。找了一本用英文写的希腊文文法书,自己就试着往下学;因为没有老师可以请教,经过一段时间积累下来的问题无法解决,最后只好放弃。学不了古文字,就转而自学德文。我买了一本北大德语教研室编的《大学德语课本》(第一册),自学起来。毕竟现代语言比古语文容易多了,这次自学为以后几年从师学习德文打下了一个初步但扎实的基础。
古希腊文学不会,就更觉得自己不能放松在中国古文字方面的努力,因为这是我在可望的将来(现在应该说终身)能够直接用来研读原始古文献的唯一的语文了。自从工作以后,尽管具体做的是世界史教学与研究,但我从未间断在中国文献方面的业余学习。最有保障的是一天工作下来的晚饭前或后,到住处附近的旧书店去逛一个小时左右,除一般寻找有无可购的中外文书籍外,每次的重点都在搜寻清人的小学、经学和目录学方面的著作。有些书很贵,买不起,就每次看一些,总要看到有一个大体了解才罢手。对清代著名学者年谱,每见一部,都要浏览一遍。这样就逐渐积累了一些最基本的清人小学、经学著作。
我买书的原则是,在买得起的里面挑版本印刷最好的,但也没有名贵好书。我常对人说,自己买书几乎像旧社会挑女婿一样,左看右挑,经过许多回才很吝啬地买一本。其实不是吝啬,这样买来的书,未到家,你对它的大体内容、功能特点都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以后用起来效率高,有时一本能顶好几本用。这一点可怜的体会,也许是有钱大手大脚买书的人无法感受的。直到“文革”开始前,我这一逛旧书店的习惯一直坚持十几年不断。“文革”后,由于工作需要,我又同时兼做中国古史教学与研究,之所以不觉突然,实在与此有关。
(十二)学问的精神土壤
我一直坚持学外文。从东北进修回北师大以后,我一面跟张天麟先生继续学德文,一面又和教研室里的几位先生一同跟一位老师学拉丁文,学了不到一学期,运动风暴到了,只好停学。这一停,从此打断了我学拉丁文的路。
学拉丁文不成,是我学古文字的第二次失败。这次失败使我想到没有希腊文、拉丁文的素养,而从事希腊、罗马史研究,究竟能做到何种深度的问题。原来我就打算以希腊古代史、印度古代史和中国古代史为三个支点,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推动自己对整个世界古代史研究水平的提高。这时就想更快地深入古印度史领域,借助自己在阅读中国古文方面的一些有利条件,来做一种有中国人自己特色的古印度史研究。
既要认真治古印度史,就不能不认真读书。我知道,真要做古印度史,不能不学梵文和巴利文,系里领导也曾经答应送我去跟季羡林先生学几年梵文。可是,先是“四清”,接着就是“文革”风暴,我的古印度史研究都被打断,更无论去从师学梵文了。
到了“文革”中后期,因思想“保守”跟不上“形势”而靠边站的人,空余的时间就稍稍多了一点。我也讨了这个便宜,想学习的心又按捺不住了。一位外语系的老师,和我是多年交流外文学习经验的好朋友,这时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各自自学起梵文来。自学不到一年,又重蹈了以前学古希腊文的覆辙——做练习中积累下的问题无法解决,不知自己做的练习是对是错,再次败下阵来。这一败,彻底打破了我学外国古文字的梦。心里不服,知道电台广播教法语,就又跟着学法语,从初级班到学完中级班,再次用英、俄、德文本的《共产党宣言》对照法文本读。还没有读完,“文革”结束,各种工作压力一齐来临——我又正式兼做中国古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所以刚学的法文就丢生了,还不如学希腊文失败后学的德文。噫,夫复何言!总之,我学外文几十年的情况是,教训多于经验,失败多于成功。一些好心的师友为了鼓励我,说我会多少种文字,使我十分惭愧。这里赘述数语,也是为了正视听于万一,以免虚声欺人。
虽说“文革”中后期有学梵文的失败,但我在中国古文献方面却颇有进展。1971年春,我被借调到故宫博物院临时帮忙(做重新开放的准备),开始下了学校里“运动”的车,在那里读了几个月古书,也从此时开始自学金文。因为有一点《说文》的底子,所以入门不觉其难。秋季回校,参加外国历史书汉译的工作,随后就参加刘知几《史通》的译注工作。译注《史通》,在当时算是注“法家”著作,可以比较集中精力。这项工作做了一年多,我的文字训诂能力得到了一次严格的考验和锻炼,原来在这方面做的准备一时都派上了用场。
1979年末,我奉调到史学研究所从事中国史教学与研究,在所里招收的硕士研究生是中国古代史专业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方向。1986年历史系建立了世界上古中古史博士点,我在系里就招收世界史专业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所以,从八十年代初起,我就正式与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早期,我曾经给研究生系统地讲过“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课,但那只是讲社会经济和政治史方面的比较,未能涉及思想文化。好心的友人劝我就此写成专著,可是在我看来,如果事先没有做好一系列专题论文以为基础,遽尔就写专著,那么这样的“专著”就恐怕只能加上引号了。学校的出版社几度和我商谈,要我把讲义整理出版,我也以同样的理由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个根本性的想法,就是比较研究是一种看来容易而实际又很难的工作。说容易,是因为只要你头脑灵活,随便在一个有话可说的方面抓一个热题,尽兴发挥一通,也能引起某种轰动效应;说不易,则是因为要真正地做比较研究,那还需要先有两种准备。这就是,第一,对于所要做比较的领域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对中外历史没有一个大体的把握,不能率尔操觚;第二,必须至少对一个国家(能多当然更好)的历史具有直接从原始资料入手做独立研究的准备,并做出了一定的成果。
我用这两项条件反省自己,觉得对于世界古代文明史,自己还是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和把握的,对于古希腊、古印度有一定程度的深入,但是已经不可能再具备从原始文献研究的能力。中国古文明是我们自己的文明,是我的精神自幼即寝馈于其间的文明,自觉理解较深,也具备从原始文献入手做研究的一定能力,最需要的是在中国古史方面做出一些切实的研究成果来,积累起一定的研究经验。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具体的研究取向,就是把中国古史的研究同经学文献研究结合起来,这是为了从源头上探寻中国古史的精神来龙,也是为了借助经学在文献考证方面的经验与成果。
二十年来,我写了一些文章,大体都不出这个路数。这样的做法,是对是错,自己不敢断言,但作为一种选择和尝试,则未为不可。曾有一位师长和我开玩笑说:“你从世界史逃到中国史去了。”我说:“我没有也不敢逃,我是在‘转进’。”这些年来,我所写的文章,有少数是直接讲中外古史比较的和比较研究理论的,多数是专论中国古史某个具体方面或问题,但是其中总寓有比较研究的含义,文中也不时有一两句指出所资比较之所在。因此,在一定限度里说,我的中国古史方面的文章都具有某种中外比较的背景。现在,我不再就外国史某一专门领域做专门的研究,但是不放弃尽可能读一些外国新书,参加或主持一些世界史教材的编写工作,把自己在中国古史研究方面的或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方面的点滴成果引进到这些教材里来。所以,我才敢说:“我没有也不敢逃,我是在‘转进’。”
我自知在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方面成果甚少,尤其不能也不敢望前辈学贯中西的大家之项背于万一。我只是多少做了一些事,还要请各方面专家多多批评指正。
我希望在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方面不断有新的专家和专著出现,我更希望的是这种研究是潜心的、踏实的、真正的研究。我常想,前辈学贯中西的大家为什么能达到那么高的学术境界?有一点至少是明白的。他们都在自己本国的文化领域里具有深厚的基础和功力,因而他们在探研外国历史文化的时候也就能自其大者、自其高处而观之,而理解把握之。他们学外国学问的时候,在精神境界上不是作为一个初学者趴在地上一点一滴地拾人遗穗,而是在本国学问上与外国学者(他们在其本国学问上)站在平等的地位上的。当然,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不能在中国历史文化方面先奠定基础就开始学外国历史文化的现象也常会发生,这也未为不可。重要的是,当一个人在外国文化方面有一定造诣以后,不宜忘记学习本国文化;因为不管自觉与否,这总是我们的精神植根最深的土壤。离开这块土壤,我们的成就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很大的限制。我深深景仰前辈大家的那种风范,愿意景行行止,也愿意与有志于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青年朋友们共勉。
(十三)我的读书心得
年轻的同学经常问我怎么读书。我想自己一辈子都在读书、做学问,关于读书,还是有一些话想跟大家谈谈的。
读书要有目的。读书的效率取决于读书的目的是否明确,也就是我们是为了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解答什么样的问题而读书,即韩愈所说的“解惑”是也。但是必须谨记:读书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对于现实问题的求解。再则就是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要写文章,写文章也有相应的要求,那就是在你的文章中,你能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如果你提出的问题司空见惯,就绝对没有写文章的必要。读书是一场激烈的智力、智慧的竞争,不仅和身边的人、同等专业的人、国内的相关专业的人士,还要和国际上优秀而杰出的思想者、学问家们进行竞争。就如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与对话理论”,如果没有竞争精神作为奠基石的话,他的理论就是浅薄的。另外,读书应当注意汲取经济学的有关法则,不做无用功;节约时间、节省精力,同样是读书过程中要留心的事。
还必须明确的是:不同的书,应当有不同的读法。荀子在《劝学篇》一文中指出:“古之学者读书为己,今之学者读书为人。”看起来,似乎后者更加高尚,更值得效法。其实不然,读书首先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人,一个知识结构、道德人格结构完善的人,否则就会成为“书蠹”,成为知识的贼人,所以荀子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在“小人”那里,读书反而会成为换取口腹之欲的方便工具,甚至成为谋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反思我这么多年的读书,以此衡量,真要冷汗涔涔而出,如芒在背的感觉十分深切。所以,读书必先为己,为己者,乃是首先要求自身的完善,非为苛求于别人,唯其如此,然后才谈得上读书为人(他人)。
关于泛读和精读,首先要找准自己现在所处的“方位”。当你走进浩瀚的书籍海洋的时候,就如一名旅客乍到陌生的城市,如果不清楚自己现在所处的方位,就会迷路,迷失自我;就读书治学而言,就不能够明晰自己当前的学术位置与层次。失去了准确的定位,读书则如在沙漠中寻水,很难实现开始所拟定的预期目标。此外,要能够看出一本书的框架和网络,寻找它们的连结点,进而寻求入山的门径和道路。
泛读是在为你将来的学术研究搭建宽广坚实的平台,是检验一个学者知识储存库的利器,就如同金字塔的塔基,其重要性自不多言。我想重点说说精读,精读可以大大提高阅读能力,精读的目的就是要切实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范围要小,防止漫天撒网,无端虚耗有限的精力与时间。在精读的过程中要一再地追问如下问题:这本书为什么这么写?它的结构、用意、表达的思想等等……精读要求对所读书籍的总体结构有深刻的了解,依此类推就是对它的篇章结构、段落结构、字词、重点词的词源,都要进行一番来龙去脉的调查研究。加强精读的训练,就好像是为了砍柴而磨刀,看去很笨,效率却很高。
要打破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的文人艺术家式的随意读书的风气。我们做研究的人需要的是科学严谨,浅尝辄止的欣赏性的读书有百害无一益,对此需要慎重对待,严加防范。要像古人读书那样,做到“入乎眼,箸乎心”,书进脑中立时分解,要能念出书的结构,提高自己的自觉分析能力。进度虽慢,必须坚持,长此以往,方可逐步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某种意义上说,精读实际上是一种有效而艰苦的学习方法的训练过程,是寻找“解牛之刀”,是提高读书效率的关键。
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和《书目答问补正》两书,皆为薄薄的小册子,但却是治史学读书修学的便利门径。通过对这两本书的阅读,和翻阅它所涉及的相关书籍,会让你对传统的典籍、相关校注的基本情况有清晰的了解,特别适用于刚刚入门的人。
然后,再去通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你就会做到心中有数,而不至于被四库全书的繁复书目所吓倒。关于“追溯法”,具体做法是重视你所看的书籍的参考书目,从参考书目中得知诸多你当下所关注问题的相关资料,实在是一种触类旁通的经济型的读书方法。这样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就会找到丰富的解决问题的材料。这种方法忌“漏”,要清楚地知道书的利用经过,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才是深入的读书,才会让你学会对书籍的最大效率的利用。
对于工具书的使用,务必要留心字典前面的凡例。了解这本字典编者的编写用意,和它与相关工具书的不同功效,这样就能够让你迅速地掌握工具书的使用。熟练以后,就可以让字典等工具书发挥最大的功效。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总是有限的,所以掌握一定的方法,进而最大限度地提高读书的效率,是读书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读书,找材料是目的之一,但不是全部。找材料凭电脑网络就足够了,但是由此而来的材料的上下文是什么,却是不得而知的事情了。西方的很多汉学家就是通过电脑找到很多材料,然后拼接组成“煌煌大著”,看去很能“唬人”,对初学者而言,有时难免会目迷于五色,失去自己的独立判断能力。现在看来,如果我们对这些著作严加审查,就会发现其间的很多“巨著”原来不过是纸老虎——这也从反面告诫我们,要时时警惕那种不够科学严谨的学风的滋生,要注意选取材料的前后关联,即西方语言学中经常提到的“语境”这一术语。
读书作为一种具有竞争和挑战的对话行为,我们可以通过书籍实现和古今中外顶尖级人物的高层次对话,明师难求,书籍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尤其,当我们很难寻找到明师的时候,书籍、读书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
另外,读书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发现自己缺点的过程。仅仅从书中看到它的不足还是远远不够的。老子说:“为学日益(知识学问),为道日损(缺点),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要从书中看出自己的不足和缺陷,所以读书的过程既是一个增加的过程,又是一个减少的过程。增加的是新的知识、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减少的是自己的缺陷和不成熟的地方。这样,长此以往,学问将会渐入佳境。多年的治学经验使我认识到:只认读书一条,而不是从一家、一人学习知识。通过广泛的阅读可以使读者同众多的高手交流对话。人类文化能够不断地发展,就是因为真理永远在我们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