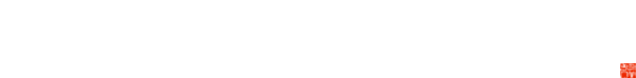张贵永(1908~1965),字致远,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史学系,入柏林大学深造,1933年获博士学位,后赴伦敦大学研究西洋史。1934年任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讲授西洋史。1949年后任台湾大学教授,1953年兼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1955年参与创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并任研究员,1962年担任中国文化学院首任史学系主任。期间,讲授欧洲外交史、西洋现代史等。他除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和《教务教案档》外,还有《西洋通史》三册、《史学讲话》,以及关于德国和西洋史学史、外交史等专文几十篇。无论在大陆还是居台期间,他都致力于西洋史教学与研究,多涉西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如今书写国人研究西方史学成就,不能不涉及其贡献,事实上学界已做出努力。王尔敏的《张贵永先生及其西洋史学论述》①,以张贵永对于近代史学界南港学派的贡献为切入点和落脚点,用大半篇幅讨论其西洋史学研究;王尔敏从通论角度梳理张贵永关于西洋史学涵义、方法的论述,从历史哲学角度述论他对于两元神学史观、唯物史观、实证主义历史观、唯心主义历史哲学、表现主义历史观、人文主义历史哲学的引介,从史学名家和思潮角度讨论张贵永关于赫尔德②、兰克和汤因比③的论述,可谓贡献良多。李孝迁的《兰克史学与中国现代史学》④、《〈史学原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⑤、《汤因比〈历史研究〉在华之传译》⑥,均触及张贵永的西洋史学问题,保持其一贯的传播视角。他们的工作,是继续探讨张贵永西方史学研究的基础。
不过,就此课题而言,一些地方尚待扩展或细化。张贵永的师承问题,不容忽视;他条理德国史学发展线索,值得关注;他尤重历史主义,不可淡化;汤因比的文化观念、西洋外交史研究,在整体的世界史意义上为一体,张贵永为此付出心血,要加以重视。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讨论。同时,张贵永关于史学涵义、对象、方法的论述,还可从不同角度继续分析,以求新意。总之,本文拟就上述诸项再行探讨。
一 治西方史学的师承:从孔云卿到梅尼克、古奇
张贵永在回忆录中提到,清华求学期间受三位老师影响,其中对其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和王国维,另一位则是陈寅恪⑦。梁、王、陈的学术影响力,为学界公认,张贵永作为清华学子,不能不提及他们,事实上他们是否引导他走向研究西洋史的道路,极其值得怀疑,因为从其回忆中看不出梁、王、陈跟他后来的学术之路有丝毫关联。
倒是其同窗黎东方在给张贵永《史学讲话》所作的《序》里,流露出蛛丝马迹。他说:张贵永“承接了孔云卿先生的衣钵,也颇为曼纳克教授所喜爱”⑧。据其所言,张氏师承主要来自国内孔云卿和德国梅尼克⑨。黎东方说,1925年,张贵永入清华大学史学系,与晚他一年的黎东方同属西洋史组,受业于留德的孔云卿(繁霱)、留美的刘崇鋐(寿民)和美籍学者马隆(G. B. Malone),得以学习德国史学,瑟诺波司(Seignobos)《史学入门》以及英国史、美国史等。对于黎东方这一说法,张贵永有所印证:
为了想彻底了解中国衰弱的病根,并探求西洋文化的根源,就在大学第二年,选修“西洋近代史”,并且花了整个寒假的时间,把德国民族史家特勒起克(Treitschke)所著的七大本《十九世纪德国史》读完,还作了一篇报告。同时,对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著述,也浏览了不少……大学第三年,我选修了西洋古代史,对于西方的古代文化、古典精神,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在文学方面,则开始爱好歌德的作品……德国历史学派之中,十九世纪语文考证学派,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兰克(Ranke),即是因此成功的第一流西洋史学家;以研究罗马碑铭石刻而奠定史学界地位,并以《罗马史》荣获诺贝尔奖金的蒙姆森(Monmsen),这两位十九世纪的德国史学家,则曾以历史研究所,训练学生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他们的弟子,甚至再传弟子,多半都在日后的史学界,崭露头角。我就在这些德国史学家的研究精神的熏染下,决心到德国去研究史学⑩。
看来,黎东方关于他和张贵永进西洋史组,学习德国史学史和史学方法这一说法,是可靠的。可是,张贵永在这里仍未透露其之所以选西洋史及其以后发展情况跟清华的哪位老师有直接关系。要弄清此问题,当然还需要继续搜寻其他证据。不过,回到黎东方那里再加考量,或许可以理出线索。
黎东方提到的孔繁霱(1894~1959),字云卿,山东滕县人,1917年留学美国,1922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翌年赴柏林大学研究院深造,1927年回国,受聘为清华大学史学教授,讲授西洋史。孔繁霱既在德国留学,又在清华教授西洋史,而张贵永选修西洋史,对德国史学情有独钟,且毅然留学德国,因此,如果说他没受到孔繁霱的引导,那简直无法理解。情况完全可能是,在孔繁霱影响下,张贵永才服膺兰克及其后学德国伯恩汉(11)和法国瑟诺波司的,尽管他没有明言自己跟孔繁霱的关系。事实上,朗格诺瓦(Langlois)和瑟诺波司的《史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是伯恩汉《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的翻版。张贵永承认:《史学讲话》“叙述史学理论及方法部分,主要依据班汉姆的《史学导论》(Ernst Bernheim,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12)伯恩汉的《史学导论》是其《史学方法论》的改写本。张贵永的《史学讲话》中,第一篇《史学的涵义及其问题》,文中明示其关于史学方法论的普通参考书前三者分别是班汉姆的《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和瑟诺波司的《史学导论》。其第三章《史学方法纲要》,关于史料的论述,例如史源学问题、史料考证问题,完全来自伯恩汉和瑟诺波司。至于为何《我的史学研究兴趣》没有提及孔繁霱,不敢妄加揣测,尚待来日深究。
据张贵永自述,1929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他赴柏林大学历史研究所留学。在德国,他尽管以关于菲特烈•赫尔斯坦外交政策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然而“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兴趣,仍然很浓,例如对迈纳克三大部巨著中的两部《大同主义与民族国家》与《西洋近代史上的国家利益说》,我都加以熟读。另一部《历史主义的起源》,则是在一九三六年出版后,他寄赠给我才读到的……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的一年间,我又从事研究兰克的生平与著作”(13)。
他所说的迈纳克,即今天所谓的梅尼克,是20世纪德国史学巨擘,奉兰克为精神导师,师从德罗伊森(Droysen)、狄尔泰(Dilthey)等人,从史学出发研究哲学,撰写政治史和思想史。他曾主编《史学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担任帝国历史协会(Historische Reichskomission)主席,晚年主持西柏林自由大学。其主要历史著作除了上文张贵永所提之外,还有《从斯坦恩到俾斯麦》(Von Stein zu Bsimasck)、《世界大战问题》(Probleme des Weithtreges)、《普鲁士与德国》(Preussen and Deutschland)、《国家与人格》(Staat and Persoelichte)、《普鲁士—德国的人物与问题》(Preussische-deutsche Gestalten und Probleme)、《历史主义的危机》(Krisis des Historismus)、《历史意识与历史意义》(Vom Geschichtlichen Sinn und Vom Sinn der Geschichte)等。
张贵永这样评价梅尼克:“他的人格为德国思想家与一般人民所共同敬仰,不论在他生平的早年或晚期均能如此……他始终不失为德国人民,尤其一般青年学子的精神导师。”(14)由此可见,梅尼克在张贵永心中地位之崇高。由于这一层关系,1965年,张贵永受聘为西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并于西柏林去世。关于他所受德国影响,曾任西柏林自由大学文学院院长的何尔宓(H. Helbig)教授一语中的:“他的早期关于《历史主义本质》、《赫德的历史哲学》和《哥德与历史》等的著作仍然带着在德国留学时所接受的思想色彩。”(15)张其昀甚至说:“他是曼纳克的嫡传。”(16)这正好印证了黎东方的观点。
张贵永在西洋所受影响还有一项,未被世人注意而为他自所言明。他回忆道:1932年暑假访问伦敦档案馆,并在伦敦大学从事历史研究,会见古奇(G. P. Gooch, 1873~1968)。他所说的古奇,擅长英国史、欧洲外交史,尤用心于19世纪史学史,曾主编11卷《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英国档案》(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著有《剑桥英国对外政策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先后编辑或主编《现代评论》(The Contemporary Review)达50年之久,所著《19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蜚声国际。张贵永回国后一直与他保持联系。古奇除编辑史料外,还做外交史、史学史,张贵永与他极为相似,而且与梅尼克的学术领域雷同。1947年,张贵永一度赴英国讲学,受聘为伦敦大学历史学研究所与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这完全得益于此前的伦敦大学之缘。
上文述及,无论在中央大学还是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张贵永都致力于西洋史。此外,据王尔敏追忆,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期间,张贵永给青年同仁开出的讲座有“西洋外交史”、“陶恩培的政治史学经验”、“赫尔德的历史观”、“俄国对东方的外交政策”、“俄国对远东、中东的侵略政策”、“研究近代史应注意的问题”、“曼纳克(Friedrich Meinecke)及其思想史的研究”(17),可见,这些讲座也多为西洋史学、西洋外交或者西洋现代史等。这完全得益于他在清华大学、柏林大学、伦敦大学的研习。
其中,著述《西洋通史》,是根据赫伯特•费歇尔(Herbert A. L. Fisher, 1865~1940)《欧洲史》(A History of Europe)编译而成,作为其在台湾讲授世界史的教科书。《史学讲话》是其自编文集,所收为史学理论与方法、西洋史学方面的论文12篇。其几十篇论文,除部分收入上述《史学讲话》外,还部分收入《张致远文集》。后者是他去世之后,台湾国防研究院和中华大典编印会共同编成,所收除西洋史学史外,还有其外交史研究方面的论文,特别是用西文写成的文章,不过其西洋史学部分多与《史学讲话》相重。
其实他还著有《詹森与中美关系》。他研读《美国外交关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中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詹森(18)大使个人信札及其向各类机构作的报告,对民国初期之中美交涉加以分析与探讨。据其本书《前言》,当在1963年完成,而据王云五《编印人人文库序》,应在1970年代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他还有一些文章散见在其他各处,为上述文集所未收。
德国史方面:《瓦解与复兴:德国民族解放战争所给我们的教训》,发表在《新民族》1938年第1卷第3期;《战后德国的命运》,载于《华声》1944年第1卷第5~6期;《德国与欧洲和平的再造》,刊登在《客观》1945年第14期;《德国的再统一与柏林问题》,公之于《新时代》1961年第7期。
匈牙利史方面:《一世纪前的匈牙利革命运动》,刊于《中央日报》1956年11月13日第六版《学人》第七期。
西洋史学方面:《评“历史学主义的起源”》,发表在《中德学志》1940年第2卷第4期,同篇文章又题为《历史主义的起源》,载于《图书月刊》1941年第1卷第1期;《历史主义的前驱》,刊登于《中德学志》1941年第3卷第1期;《历史主义的先锋》,发布在《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1941年3月3日第121期;《启蒙运动的历史思想》,则载于《学灯》1941年3月10日第122期;《莫赛与赫德的历史观》,发表在《中德学志》1941年第3卷第4期;《陶恩培的历史研究》(上),刊于《中央日报》1956年10月9日第六版《学人》第二期;《陶恩培的历史研究》(下),则刊于《中央日报》1956年10月16日第六版《学人》第三期;《赫德的历史观》,刊于《中央日报》1956年11月27日第六版《学人》第九期;《历史是追求真理的学问》,登载于《中央日报》1956年8月5日第八版;《歌德与历史》,连载于《中央日报》1957年2月5日、2月12日的第六版《学人》第十九、二十期。
自述性文章:《出席亚洲史学会议的经过和感想》,发表在《新时代》1961年第1卷第1期;《我的史学研究兴趣》,载于《新时代》1962年第2卷第1期;《第二届亚洲历史学家会议报告》,刊于《新时代》1962年第2卷第11期。
译著:Hermann Oncken著《印度的安全》,发表在《中德学志》1940年第2卷第1期;KarlBrandi著《中古史与近世史》,载于北平中德学会《五十年的德国学术》第二册。
本文撇开其研究西洋历史不论,而探讨他关于西方史学的研究。
张贵永所讨论的史学涵义、对象、范围和方法等一般性史学问题,都是对西洋史学史的梳理、分析和总结。
历史学的涵义。张贵永有明确的历史学定义,他说:“史学是以心理的与外界的因果关系,根据当时的共同价值观念,来研究与叙述人类团体活动在时空中的演进事实的学问。”(19)
他强调:求知是史学的主要目的;历史因果分析既有心理的又有外界的;史学不仅要关注普遍的,并且关注特殊的;历史研究指向群体而不限于个人;历史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观念都是必需的。其实,张贵永的定义中还有一点,那就是历史学代表着一个时期共同的价值观念,尽管他没有强调,然而还是要替他指出。每一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的价值观念,它一定会反映在历史学中,因此,界定历史学不可忽视价值观念(20)。
他的这一定义,是建立在研究西方史学观念发展基础上的。第一,通过考察“历史”的词源,得出“历史”字义指事实经过或研究事实经过的学问。他指出,希腊文Historie原始意义为研究或者已研究了的知识,具备今天“历史”的含义,德文Geschichte有“经过”和“研究经过”的意思(21)。因此,张贵永概括出“历史”的上述含义。第二,通过总结西洋近代以前史学发展史,得出结论:历史学经历了只注意纯粹历史记载,到关注获取历史教训,再到追求学术性即明了事实的因果及其相互关系,直至走向成熟。从古代到18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表明历史学是依据事实,赋予价值观念的认识历史的学术。第三,通过梳理19世纪以来历史哲学的发展,认识到历史学与哲学结合是必然趋势,因此历史学家在选择材料时必须有价值观念的存在,历史学与哲学互为辅助。据此可推论出:历史学同时关注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必有价值观(22)。
张贵永的因果、人类团体、时空事实观念,与当时一般实证主义史学有通性,但其共同价值的观念,又别具一格。
历史学的对象、范围。一般实证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张贵永则有所保留。他区分理论与实践层面的研究对象,认为:“在理论上,我们学问包括人类各方面,各种社会的与团体的活动,所以文学、艺术、经济学等都可属于历史的智识范围。”但是实际上“研究范围多大,研究的哪一方面,须看本人的实际兴趣,及所具有的专门训练与能力而定”(23)。可见他与一般的实证主义史学家同中有异。需进一步确定的是,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在哪里?张贵永开宗明义:“历史属于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不仅材料不同,方法亦不同……对于历史的真实内容、特殊的事实,与演变的情形,都不能应用普遍定义与普遍定律……不能像唯物主义与实证主义说的可以直接当作自然科学。”(24)另外,他在《历史是追求真理的学问》中,从艺术与科学的双重意义上谈论历史学,认识到“科学的理智和艺术的情感往往在历史著作里不能融洽无间。史家的文体愈动人,接近真理的兴趣也就愈减损……另一方面精心钻研的史家,尤其是终身以考据为专业的学者就不免枯燥乏味”(25)。文章结尾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追求真理还是由科学主义史学来承担。这似乎表明其结论有摇摆,兴许是他在那个科学主义盛行时代的无奈。无论如何,总体上,其观点与包括实证主义史学在内的科学主义史学主张完全不同,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正像王尔敏所言:“在50年代,科学主义(scientism)盛行之际,多数史家倾心于科学治史,并有人在同时代声言将史学提升到自然科学地位。在此流风之下,张氏这样申言,自是启聩发聋,实如朝阳鸣凤,在中国学界有先见,正代表一个引路明灯。”(26)可是,他主张历史学使用多种辅助学科,又与实证主义史学主张完全一致。在历史学的对象、范围这个问题上,同样表现得与一般科学主义史学家同异互见。
历史学的价值。在《史学的涵义及其问题》中,他说历史学的价值可分三种情况:第一,在普遍演进史观中,历史教人根据普遍的演进关系,去观察个人或社会团体活动,明了人类全体和个人与国家间的关系;第二,历史学与实际的审美旨趣有联系;第三,历史学是其他各种学问的辅助手段(27)。另外,在《历史学的教育价值》一文中,他又说:“历史主要的价值与目的,还是教育大众。”具体说来,他认为,“历史是人文教育的基础”(28),此外,它的价值在于可以满足人们关于过去的好奇心,还可以“对现在所能给予的资鉴”(29)。这些主张,跟20世纪其他史学家尤其是实证主义史学家并无二致。
历史学的方法。在《史学方法纲要》中,张贵永是这样定义史学方法的:“史学方法就是把材料变做智识的工具与途径。”(30)它包括史源学(即史料研究)、考证、解释、组织(即历史的综合研究)、写作(即著述)各环节。史源就是原始材料,主要有三种,即直接观察得到的,靠口述、书写和图画等方式报告下来的,和事实经过的遗迹(31)。而考证就是要“断定史料的实际情形及其记载的内容”(32)。通过外证确定史料本身是否可靠,通过内证确定所记载的事实可靠程度,采取各种办法鉴别伪造与错误。解释,就是“史料内容的诠释,有狭义的(训诂)与广义的(推理)应用方法”(33)。组织,张贵永也视为历史的综合研究,就是“必须从全体发展的关系来解释”(34)。写作或者著述,是“把研究的结果明晰地表达出来……就是始终得保持学术的立场,简洁流畅,而能无损于考证与综合研究的历史真相”(35)。其详细的论列,这里不再赘述。就历史学方法而言,张贵永几无创见,因为他几乎全部照搬了伯恩汉的《史学导论》。
二 一以贯之的历史主义:从先驱到梅尼克
张贵永重视思想史研究,关注西洋近代史学发展史,这样历史主义就成为他不能不涉及的主题,特别是他受梅尼克影响,十分关注历史主义,梳理了它从起源到当代的演变历程。他关于历史主义论述,从评论梅尼克的《历史主义的起源》开始,又以讨论梅尼克的学术思想而结束。
其《评“历史学主义的起源”》,上文已述及,可析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述梅尼克学术生涯、地位及晚年内心冲突和《历史主义的起源》的写作;第二部分,追述历史主义(Historismus)词源,梳理词义演变,界定历史主义的核心因素为“个性”和“演进”(36);第三部分,指出《历史主义的起源》的方法既以问题为中心组织材料,又不失变生动的历史为空论,概述其内容为:梅尼克以莫塞(Mōser)、赫尔德和歌德为个案和落脚点,并作为背景叙述英法启蒙运动史家、先期浪漫主义的激荡、天赋人权思想、基督教及其革新、自然科学等,涉及史学家、思想家有沙夫茨伯里(Shaftsbury)、莱布尼兹、维柯、伏尔泰、孟德斯鸠、休谟、吉本、罗伯逊等。张贵永此文虽名为评论,但实际上只是简介。
他论述了历史主义的先驱。这以发表在《中德学志》1941年第3卷第1期的《历史主义的前驱》最为集中。另一篇是发表在《学灯》1941年3月3日第121期的《历史主义的先锋》,前半部分为《评“历史学主义的起源”》的第二部分,后半部分与《历史主义的前驱》多有文字出入,但是主旨、材料和句式均同,故其差异不足为论。他认为,笛卡尔和洛克的思想促成历史主义先驱的产生。历史主义先驱主要有莱布尼兹、沙夫茨伯里、维柯和阿诺尔多。莱布尼兹的《人类悟性新论》,承认多元及其和谐统一,并与延续律相连接,回归新柏拉图主义。莱布尼兹这种个性观念的意义在于,“无论对于德国的启蒙运动以及日后的唯心主义与历史主义,他都是擎起炬火的先锋”(37)。沙夫茨伯里也是一位新柏拉图主义者,其思想核心是精神形式与力量联合创造生命形态,“最先承认个性原则”(38)。维柯则一方面肯定人创造和认知历史,另一方面肯定历史的演进,具备后来德国历史主义的两个因素。阿诺尔多把世界观和历史观当作“心灵的天赋权力”,“在历史学家中间确是第一位把人的心灵放到历史生命的中心点去……这又是历史主义的培养土壤”(39)。张贵永的这些意见甚为中肯,但稍嫌简单,缺乏具体分析。
他论述了启蒙思想中的历史主义意义。这最早见于其发表在《学灯》1941年3月10日第122期上的《启蒙运动的历史思想》。问题是,这篇文章结尾注明“未完”,事实是,他确实比较充分地论述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的思想对于历史主义的意义,可是在提到休谟、吉本和罗伯逊之后才刚刚开始对休谟的论述,文章就戛然而止,显然文章并没有囊括启蒙运动的主要学者。关于伏尔泰,他认为其对新的现世生活的愉快感觉、自然主义和其社会伦理思想,使得在伏尔泰那里,历史学的价值是为了启蒙人类,历史写作免不了戏剧家的作风,描写铺叙,富有色彩,这些为历史思想争得独立自主的地位,特别是他注重时代精神和国家利益,为兰克所坚持。关于孟德斯鸠,张贵永以为孟德斯鸠揭橥民族精神,主张根据各国特殊实质利益和条件来洞察一国法律,是其法权思想个性化的体现;特别是“他对于罗马历史命运的观点简直就是政治的相对主义,而为日后历史主义的开路先锋”(40)。关于其他法国学者,张贵永简单提到杜尔格、孔多塞影响了赫尔德和歌德的演进思想;卢梭的违反习俗,坚持个性,以自然为归宿,但是在历史世界中没有找到类似的路数,因此他所唤醒的历史主义个性观念,仍拘束在正统的天赋人权的精神里;关于休谟,张贵永认为休谟缩小了天赋人权的范围,分辨真理与谬误,并以情感和兴趣来考验,这就是休谟的怀疑态度,特别是反对因果律的必然性,主张事物之间在习惯的蜕变、前后承变中发生关系,这与日后的历史主义有着关联。张贵永对这些学者的思想与历史主义之间的关联,条分缕析,很明晰。
他论述了英国早期浪漫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关联。在《从英国先期浪漫主义到赫尔德的历史思想》一文中,张贵永特别提到莎士比亚影响了格雷(Thomas Gray)、华尔坡尔(Horace Walpole)对中世纪哥特式艺术发生兴趣,还提到司各脱的历史小说、白勒克韦尔(Blackwell)的《荷马史诗》研究、罗斯(Robert Lowth)的《圣经》中希伯来圣诗研究、伍德(Robert Wood)的《荷马史诗》研究、胡尔特(Hurd)关于骑士精神与故事的信,都影响了赫尔德、歌德的历史主义,他说:“这些新的深入情感与富于幻想的创作,诗和艺术具有引入历史主义的思想情绪。”(41)就历史学而言,张贵永认为弗格森和博克尔对于历史主义贡献最为突出。弗格森的主题是国家观念在历史上的意义,这对于历史主义至关重要,而博克尔把审美艺术的观点引入历史研究,热爱现世并虔信,这些在德国分别由莫塞和歌德来实现。它们“在兰克精神修养的过程上密结不离地相互影响”(42)。这里与他论述历史主义先驱一样,颇为简单。
他论述莫塞、赫尔德、歌德等人与历史主义起源。《从英国先期浪漫主义到赫尔德的历史思想》一文,把德国精神运动中的学者分两类,一类以莱辛、温克尔曼、席勒、康德为代表,他们不是典型的思考历史的人,但却对历史思想做出了贡献;另一类以莫塞、赫尔德、歌德为代表,直接代表历史思想的成就。第一类学者,特别是莱辛和温克尔曼,虽然有着倾向于固定理想的思想方式,但是关注创作动机和历史个性秘密,这样就启发了历史主义。不过,张贵永讨论的重点不是他们而是第二类学者。
对于第二类三人的讨论,除了《从英国先期浪漫主义到赫尔德的历史思想》外,还有发表在《中德学志》1941年第3卷第4期的《莫赛与赫德的历史观》和发表在《国立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1945年第3卷第1期的《歌德与近代历史思想的起源》。《从英国先期浪漫主义到赫尔德的历史思想》,从论述莫塞、赫尔德、歌德开始往下,与《莫赛与赫德的历史观》大同小异,而完整性不如后者。他的《赫德的历史观》、《歌德与历史》,与上述文章内容大同小异。
张贵永指出,在莫塞身上已经看到历史主义的所有萌芽,这些正是兰克及其后学所遵循的原则。关于赫尔德,张贵永认为,启蒙运动、敬神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交互影响赫尔德,赫尔德要写出一部人类心灵的历史,以同情、感应去发现历史上的心灵生活,这就决定其历史思想是个性和演进相结合,把民族时代的个性归结于个别观察的历史全过程,其思想意义在于,“发生了四大直接影响,那就是浪漫主义,斯拉夫大民族精神,人与自然的研究,最后还有歌德的创造”(43)。歌德不仅把莫塞与赫尔德新的历史见解大规模运用,并且有意识地当作方法上的基础而用于万物;歌德认为一切生命须在其原始形式与变态中完成,历史亦得根据这一定律;歌德的这些观点被引入对民族与时代的认识;他打破世界史目的论,导致兰克的世界史观念。这些就是歌德的历史主义。最后,张贵永这样评价歌德:“他对我们永远是向高处的领导者。”(44)张贵永对这三位学者的分析颇为细致,不过他对德国学者的分类值得商榷,因为严格说来,他提到的那七位学者除了莫塞和温克尔曼,其余都不是纯粹的历史学者,因而其论述的开场就显得多余。
他论述兰克、梅尼克等人史学中的历史主义倾向。这方面的文章有:发表在《自由中国》1952年12月16日第七卷第十二期上的《兰克的生平与著作》和载于《思想与时代》1965年1月24日第一二六期的《曼纳克及其思想史研究》。
张贵永指出,兰克在历史研究过程中,从方法与史料的进步,从历史认识的进展,作者自身始终变化万千,他自己的时代也呈现出韵律从旁附和,他以真挚与深刻的同情心去认识所亲身经历的德国历史阶段,并进而影响对于德国以往历史的认识,其作为学者的生命总和民族生命交织在一起。张贵永认为,兰克这些历史主义倾向,同其路德教信仰、民族复兴情绪紧密相关,正是这两种情结与历史关联,才促使他对历史认识自主性的坚持,坚持从个别研究达到对于事实的普遍见解,从而形成对全部关系的客观认识。张贵永对兰克评价至高:“从他各方面的成就来看,真是已经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境地。从西洋全部思想史与所有精神观念出发来衡量,亦有其不朽的价值。”(45)关于梅尼克,张贵永以为,梅尼克最能体验时世,有深刻感想,与现代机械式的生活格格不入,能以真挚的热情参加政治辩论,同时又富于学术态度与高尚旨趣,以最精细的分析眼光研究普遍精神趋势与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兼具民族与世界的历史观点,且有擅长写作的艺术天赋。张贵永评论说:“他从精神内心出发坚持道德与思想的个性发展,猛烈反对权力与独裁;他曾以大无畏的精神努力挽救德国民族的命运及其文化使命,历年为德国人们的自由精神奋斗,他对于德国命运遭遇的自我批判和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态度赢得举世人民的尊敬。”(46)张贵永在文中并未明说兰克和梅尼克的这些思想倾向是历史主义的,但是他在论述他们之前的历史主义先驱或开拓者时,处处与兰克相联系,这样就可以认定他在这里谈论的兰克思想就是历史主义的,自然与兰克有着共同倾向的梅尼克的思想也是历史主义的。
他对莫塞、赫尔德、歌德等人历史主义的论述,重视其学术渊源及其相互差异,反映出他对于研究对象的稔熟。不过,从其论著来看,他显然把歌德的学术活动作为历史主义产生的标志,这样歌德之前的相关学者都可以称为历史主义的先驱。可是张贵永又明确把先驱特指为莱布尼兹、沙夫茨伯里、维柯和阿诺尔多等人,这样处理着实让人费解,也许是其研究周期过长造成的,可算是其学术的百密一疏。另外,其论著尤其是在大陆期间发表的文章,不少地方照搬了梅尼克,限于篇幅,这里不容详细举例说明。
非常有意思的是,从时序上看,其论文发表从评论梅尼克开始,又在论述梅尼克处结束,这可谓他研究西洋史学的第一个归宿点。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张贵永梳理历史主义的起源与发展,自然显露其在欧洲近代史学史论述方面的第一条主线——时间维度上一以贯之的历史主义产生发展史;同时清理出德国近200年的史学发展简史,这显示其欧洲史学研究的第二条主线,无疑对于国人今后进一步研究德国史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 世界文化视野:汤因比的史学,西洋外交史学
张贵永研究的课题,与西洋史学相关的,还有汤因比的史学观念与实践、西洋外交史研究的回顾等。
张贵永关于汤因比的论著有:《文化的起源——介绍陶恩培的历史研究》,是1951年7月19日在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第二十二次座谈会“世界文化的前途”上的讲话,作为会议纪要一部分,原载《大陆杂志》1951年7月31日第三卷第二期,《张致远文集》1968年出版,收录此文,改名为《世界文化的前途——介绍陶恩培的历史研究》。另外,根据1984年修订版《史学讲话》扉页上的介绍,张贵永自编的《史学讲话》初版于1952年,到1984年之前再版两次,前面3个本子笔者都未曾见到,是否收录《文化的起源——介绍陶恩培的历史研究》,不得而知。可是,1984年版保留的张贵永1952年所写的初版《前言》里,明确提到初版里有“介绍陶恩培历史研究一章”,由此可以推论,1952年初版的《史学讲话》,收了此文。如果说1984年收录的是对1952年的保留的话,那么文中删去他在会议发言上的开场白,其余则无区别。
《史家的灵感——兼论陶恩培的治学经验》,王尔敏说,1956年7月6日张贵永做了名为“陶恩培的政治史学经验”的报告。这可能是“陶恩培的治学经验”之误,原载《自由中国》1956年12月1日第十五卷第十一期,后收入1968年出版的《张致远文集》,应该没有收入1952年版本的《史学讲话》,之后两次修订本是否收入,因未亲见,不得而知,但是1984年版本的《史学讲话》确实将其收入。
《陶恩培〈历史研究〉的第十二本》,原载《新时代》1961年9月15日第一卷第九期,收入1968年出版的《张致远文集》。
还有一篇评介《历史研究》第七、八、九、十册的文章。王尔敏在《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中提到,张贵永在台湾《中央日报》“学人”专栏评介陶恩培的《历史研究》七、八、九、十各本,王尔敏承认并未亲见。他的说法可能来自张贵永自己的交代。张贵永说,在写《陶恩培〈历史研究〉的第十二本》之前,已写过3篇关于汤因比和他的《历史研究》的文章,第一篇就是《文化的起源——介绍陶恩培的历史研究》,第三篇是《史家的灵感——兼论陶恩培的治学经验》,而“第二篇刊登在《中央日报》的《学人》(见《学人》文史丛刊第二辑)。那是评介《历史研究》的第七、八、九、十册”(47)。可是,张贵永并未披露题名。经查证,这篇文章题为《陶恩培的历史研究》,分上、下两部分,分别刊于《中央日报》1956年10月9日第六版《学人》第二期,和10月16日第六版《学人》第三期。
张贵永对于汤因比的关注,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历史研究》全书的基本情况。关于《历史研究》第一至六卷的介绍,是在《文化的起源——介绍陶恩培的历史研究》中完成的;第七至十卷的介绍见于连载在《学人》上的《陶恩培的历史研究》;第十卷中汤因比关于其治学经验的介绍,由《史家的灵感——兼论陶恩培的治学经验》来承担;介绍第十二卷的则为《陶恩培〈历史研究〉的第十二本》。《历史研究》第十一本为图集,他未做专门介绍。这些文章涉及汤因比著作动机、研究过程和思想体系等。例如,在《陶恩培〈历史研究〉的第十二本》一文中,张贵永指出,从1921年汤因比计划写《历史研究》到1961年,40年间世事沧桑,他人史著层出不穷,世人对其毁誉有加,汤因比要重新思考,吸纳新论,答复辩难,这就是汤因比写《历史研究》第十二卷的动机。至于汤因比著作内容和思想体系,张贵永认为,汤因比依旧相信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只能由分析、比较与分类研究求其真理;汤因比大体上没有改变自己的结论,但是个别处有所变化,他改变过去以希腊或中国为模式概括一切文化的做法,采用希腊—中国混合模式以说明其他文化发展的差异。对于张贵永的这些介绍,他自评道:“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著作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书的动机,以及研究的经过已介绍了一个大概。”(48)其自我评价是谦逊的,确是实事求是的。
第二,汤因比作为历史学家的灵感。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第十卷第十三章中,叙述自己的治学经过和体会,张贵永据此提出汤因比作为历史学家的灵感问题。张贵永以为,汤因比响应神的召唤,把研究历史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汤因比相信历史学是神的启示,历史学家的颖悟同数学家、物理学家、诗人、先知一样有其特殊角度,这种信念使他几十年持之以恒地研究历史。张贵永从汤因比治学生涯中总结出,汤因比出生后60年来,殷商文化、印度文化、赫泰文化和米诺文化的发现,激发汤因比的好奇心;历史事实关系包括事实间相互关系、事实内部关系,具有神秘感,激起汤因比的研究冲动;类似的事实会使人产生类似的感觉,表现为想象、抒情等,历史学的这种史诗性、叙事性、戏剧性诗意,对于汤因比富有吸引力;探讨历史事实背后的意义,是神的启示,也是与神契合的一种努力,是历史研究的最高意义,正符合汤因比的心境。这些都是出于对造物主心灵的接近,吸引着汤因比不懈地探求历史。
第三,汤因比论人类文化的起源。在《文化的起源——介绍陶恩培的历史研究》中,张贵永分析汤因比走向文化研究的合理性。19世纪西方主流史学家例如蒙森等人钻进象牙塔,做得专精,但是忽略人类文化的精神,只能由直觉、综合研究来弥补。而且,这些专门研究,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被一些零星材料所吸引,不去注意具有更大意义的历史事物。特别是近代史学中民族主义的勃兴,政治色彩浓厚,评价历史的价值出现偏差,事实上世界历史中出现许多不同类型的文化,愈显得民族主义的偏颇。张贵永认为,这些正是汤因比的著述可以纠偏的。例如,在汤因比看来,艰难贫困地区、新土地对于历史发展能够发生刺激,这是自然环境因素,但是人为环境例如外来压力和内部逼迫,也是刺激文化起源的重要因素;环境刺激不能过于残酷,应存中庸之道,当在残酷与不残酷之间。张贵永确实抓住汤因比论文化起源的某些要点,不过还是初步的。
张贵永对西方学术界外交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张贵永是研究西洋近代史的,西洋外交史是其中重要内容,而关注西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则是治西洋外交史的题中之义。他的这方面论述,突出表现在《西洋外交史研究》中。
他十分强调外交史研究,把它看成克服民族偏见、撰写真正世界史的途径,以为兰克《日耳曼与罗曼各族的历史》、剑桥大学约翰•西莱(John Seeley)《英国的扩张》,都是把外交事务看成重于国内事务的样板。他重视外交与民主问题,这使他注意到庞沙毕勋爵(Lord Ponsoby)的《民主与外交》、杨格爵士(Sir George Young)的《外交史》和波莱士勋爵(Lord Bryce)《国际关系》中的相关论述。他根据西洋外交史学发展情况,提出研究外交史中必须注意的问题:第一,有利于外交史研究的教学条件。在这方面,张贵永指出法国巴黎政治学院造就索莱尔(Allbert Sorel)及其《欧洲与法国革命》,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成为专家研究的中心。第二,做好研究外交史的准备工作。阅读《剑桥近代史》以了解世界大势,阅读各国政治家生平,进而研究历史专著,注意各国使节言行。第三,深入研究官方档案,熟悉外交案件情况。第四,熟悉各种观点,留意政治家自白。
大体说来,关于西洋学界的外交史研究,他还停留在介绍层面,比较肤浅和零散,倒是他提出的几条关于如何做西洋外交史的认识,颇具心得,可是已经离西方史学史稍远了。不过,为历史研究计而做的学术史梳理,同样具有史学史的意义。
须要说明的是,从他所写美、英、俄、德等国外交史,以及他所提出的做西洋外交史的心得来看,他显然强调国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心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特别是人类文明的出路,这一追求,恰好与他所关注的汤因比的学术旨趣相类似。因此,汤因比的文化观念与张贵永的西洋外交史研究理念,都视世界为一整体,并关心人类文化发展的前景。可以说,汤因比是张贵永西方史学研究的第二个归宿点,它与前述归宿点梅尼克一起,成为张贵永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前途的两个出发点。
四 张贵永关于西方史学研究的学术意义
张贵永的西方史学研究,上述已见大端。今天看来,无论对于台湾史学风气转变,还是对于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它对于台湾史学风气转变具有发乎先声的意义。1949年后,台湾史学界,以傅斯年为旗手的史料搜求派占据主导地位。他以史语所所长、台湾大学校长的有利位置,网罗一批学者,从事史料搜集、考订和整理工作。然而,时至60年代,台湾学界难以扩充史料,史料搜求受到很大限制,而且欧美史学从科学史学转向对主体阐释的重视,从而影响台湾史学风气的转变。1962年许倬云留美归来,与胡佛、李亦园等在1963年创办《思与言》,倡导解释学派的方法。五四时期就崭露头角的殷海光,1964年出版《思想与方法》,主张使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也公开同史料搜求派唱起对台戏。特别是1967年许倬云担任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受史料学派排挤的钱穆从香港移居台湾,标志着台湾史学风气的转变。总之,史料学派主导地位在60年代中期开始动摇,对此,有学者指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史学的主流原本一直掌控在史料考证派手中。但自60年代起,这种局面逐渐难以维持”(49)。张贵永通过研究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认为成熟的历史学不仅要关注历史的普遍性,而且要关注其特殊性。它离不开哲学,而哲学则是价值观念的抽象,因此历史学必有价值观。他关注汤因比的历史哲学和史家情怀。他主张历史学使用多种辅助学科等。有趣的是,1965年他去世后,这些观点盛行起来。可见,他从西方史学中总结并发表出来的主张,实领台湾史学风气转变之先。
它是国人研究西方史学的卓越范例。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耿淡如就提出:史学史不是历史家传记集和目录学,应反映历史学家、历史学派在思想领域的斗争;史学史应和历史哲学史或社会思想史有区别;史学史应包括历史编纂与历史研究两者在内;史学史应结合其他相关科学来研究;史学史应总结过去史学成绩;史学史应以研究历史的同一方法来研究等等(50)。后来,张广智指出:应研究历代西方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不做成传记集和目录书;应研究西方历史学家所处的时代与历史环境;应研究西方史学流派的过去与现在、繁荣与式微、成就与问题;应在西方史学的流变中做出动态的考察,历时共时,纵横比较,上下连贯;应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的指引(51)。张贵永从欧洲社会状况出发,重视欧洲近代以来史学中一以贯之的历史主义,考察其起源、成长与影响,分析不同时期学者思想的贡献与不足。这种结合社会背景、关注学术传承、重视史学思想的研究路径,是张贵永西方史学研究实践的突出特征,在某些方面,与大陆不同时期的同仁学者所见略同,是研究西方史学的成功范例。
它对于当前中外史学交流研究具有典型意义。学界已经认同,史学史研究新的增长点,是中外史学交流史。一方面,在书写中国史学史时,自然要写某一史家、史著、史学思想与方法对于中国后学的影响,此外可增加其在域外的流传与被接受,可增加域外史学对于中国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书写外国史学史时,可增加外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可增加汉学家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张贵永本是中国学者,他研究西洋历史、西洋史学,在国内介绍、评论西洋史学,他关于西方史学的认知具有中国人独特的视角。张贵永的学术经历,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中西史学交流的典型案例,同时他所秉持的看待西方史学的眼光也特别值得当代学人汲取。这样,探讨其西方史学研究情况,无疑有利于学界借鉴其理论与方法,有利于增进和丰富中国学界关于中外史学交流的研究。
它对于一些西方史学现象的认识具有经典性。例如,兰克作为19世纪西方史学的代表,其学派具有普遍的国际影响,在欧美、中国都有传承。可是,由于17世纪开始的人类知识的自然科学化运动,因此史学界主流学者以自然科学为衡量史学学术性的尺度。兰克曾经主张“如事直书”、“排除主观”等所谓的“客观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欧美学界推为科学史学的楷模。这种倾向在中国则突出表现为史料学派,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反对解释、疏通史实。可是,事实上,兰克的史学并不是像科学史学家们所想象和推崇的那样,汪荣祖在1975年《食货月刊》三卷三期上,发表《兰克史学真相》,这篇文章改头换面后出现在《史学九章》中。他指出,英美世界误读了兰克,兰克实际具有浪漫主义风尚,有同情心但不动感情,写作民族国家历史,兰克同样重叙事,讲究行文艺术,赋予历史以意义,裁断与解释历史(52)。在此之前,张贵永业已指出兰克的历史主义倾向,同其路德教信仰、民族复兴情绪紧密相关,正是这两种情结与历史关联,才促使兰克的历史认识自主性的坚持,兰克坚持从个别研究达到对于事实的普遍见解,从而形成对全部关系的客观认识。可见,张贵永这一见解,无疑对于认识兰克及其学派的客观主义具有经典性。
当然,张贵永的西方史学研究有局限性,例如就历史学方法而言,几无创见,因为他几乎全部照搬伯恩汉的《史学导论》;论著尤其是在大陆期间发表的文章,不少地方照搬梅尼克;关于历史主义先驱的论述,稍嫌简单,缺乏具体分析;对于汤因比的认识还是初步的。此外,其研究对象也局限在欧洲近代历史哲学领域,没有像其同时代有的学者那样对西方史学做通史性论述。然而,这些正是拓荒性、专门性研究工作所常见的,无须苛责。
总之,张贵永的求学经历,导致他走向研究西洋史学的道路,其研究成果大体可分两部分:从一般意义史学上说,在史学的涵义、对象、范围与方法等方面,他所阐释的,多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流行观念,特别是史学方法部分,来自伯恩汉、瑟诺波司的相关论述。在欧洲近代史学史论述方面,有两条主线和两个归宿点。两条主线是,时间维度上一以贯之的历史主义,和空间维度上德国差不多200年的史学史;两个归宿点是德国梅尼克的学术思想和英国汤因比的文化观念,也是他思考战后人类精神世界和文化出路的两个着眼点。对此,上文相关部分有较详细述及。尽管他没有对西方史学做通史性论述,其关于历史主义、近代德国史学的全部论述,多受之于梅尼克《历史主义的起源》,一些地方稍嫌粗糙;然其研究构架与视角,在20世纪国人研究西方史学中,别具匠心,无论对于台湾史学风气转变,还是对于中国大陆的西方史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注释:
①王尔敏此文最初发表在《兴大历史学报》第十六期,2005年,后收入其《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指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曾译为“海德”、“海尔德”、“赫德”,今通译为“赫尔德”,张贵永或译为“赫德”,或译为“赫尔德”。
③指Arnold Joseph Toynbee,曾译为“托因比”,今通译为“汤因比”,张贵永译为“陶恩培”。
④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第七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⑤该文载于《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
⑥见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⑦⑩张贵永:《我的史学研究兴趣》,《新时代》1962年第10期。Thoedor Mommsen,今通译为“蒙森”,张贵永译为“蒙姆森”。
⑧黎东方:《〈史学讲话〉序》,张贵永:《史学讲话》,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2页。
⑨指Friedrich Meinecke,或译为“梅耐克”、“曼纳克”,今一般译为“梅尼克”,张贵永译为“迈纳克”或“曼纳克”。
(11)指Ernst Bernheim,旧译作“伯伦汉”、“朋汉姆”、“柏衡”等,今译为“伯恩汉”,张贵永译为“班汉姆”。
(12)张贵永:《史学讲话•前言》。
(13)张贵永:《我的史学研究兴趣》,《新时代》1962年第10期。
(14)张贵永:《史学讲话》,第210页。
(15)何尔宓(H. Helbig):《悼张贵永教授哀词》,台湾“国防”研究院和中华大典编印:《张致远文集》,新亚出版社1968年版,第514页。
(16)张其昀:《〈张致远文集〉代序》,《张致远文集》,台湾“国防”研究院出版部1968年版,第1页。
(17)王尔敏:《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页。
(18)詹森(Nelson Trusler Johnson, 1887~1954),1929~1935年任美国驻华全权公使,1935~1941年任驻华大使。
(19)张贵永:《史学讲话》,第20页。
(20)(21)(22)(23)(24)(27)(28)(29)(30)张贵永:《史学讲话》,第21~24、1、8~17、34~37、26、25、252、257、39页。
(25)张致远:《历史是追求真理的学问》,《中央日报》1956年8月5日第八版。
(26)王尔敏:《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第97页。
(31)(32)(33)(34)(35)张贵永:《史学讲话》,第41、58、66、67、73~74页。
(36)这一部分文字,稍有变化又出现在《学灯》1941年3月3日第121期的《历史主义的前阶段(一)历史主义的先锋》前半部分。《历史主义的先锋》的《编辑后语》说得清楚:“张贵永教授将这书的重要思想介绍于中国学术界,兹先发表《历史主义的前阶段》两章。”其中所谓“两章”,是指《历史主义的先锋》和《学灯》1941年3月10日第122期上的《启蒙运动的历史思想》。
(37)(38)(39)张贵永:《历史主义的前驱》,《中德学志》1941年第1期,第57、56、58页。
(40)张贵永:《启蒙运动的历史思想》,《时事新报》1941年3月10日,第122期《学灯》。
(41)(42)台湾“国防”研究院和中华大典编印:《张致远文集》,第22、23~24页。
(43)张贵永:《莫赛与赫德的历史观》,《中德学志》1941年第4期,第565页。
(44)张贵永:《史学讲话》,第142页。
(45)(46)张贵永:《史学讲话》,第156、223页。
(47)(48)台湾“国防”研究院和中华大典编印:《张致远文集》,第365页。
(49)胡逢祥、李远涛:《五十年来中国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50)耿淡如:《什么是史学史?》,《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
(51)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2)汪荣祖:《史学九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