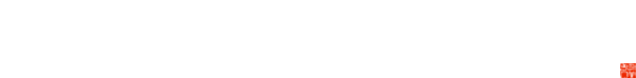爷爷是在我高考那年的夏天去世的。我却经常在秋末冬初的时间里想起他。因为,这个时间段是我们老爷俩儿的欢乐时光。
秋末冬初,秋收冬播的农活已经结束,而天气又尚未寒至冰封大地,闲不住的爷爷此时就会喊上我,牵上家里的犍牛老黑,抗上犁头,把准备来年春播的耕地犁翻一遍。这样,一可除虫保墒,二可从地里捡些秋收时的遗漏,颗粒归仓,增收添产。
来到地头,爷爷并不急于套牛耕作,而是先让牛儿吃上几口尚带有露水或霜星儿的最后的绿草,自己则装上满满一烟袋窝儿的旱烟,用火镰点上,一边很享受地吸着吐着,一边跟老黑细语,“吃吧!吃吧!快吃吧!这可是今年最后的绿色了”。
等到烟窝儿里再没有火星的时候,爷爷即在鞋后跟把烟灰磕净,把烟袋杆儿别到腰间,套上老黑,牛儿在前,爷爷在后,当中则是将泥土翻开的犁铧。我则像爷爷的小尾巴一样,紧随其后,不时地弯下腰去,捡起随犁铧翻出的花生、红薯,放到挎在胳膊上的小篮子里。几个来回下来,我的篮子里就沉甸甸的了,很有成就感。
花生、红薯,当然是我想要的,但最让我兴奋的则是偶尔能捡到蛰伏的豆虫。经过一个夏季的食绿叶喝甘露,豆虫此时都早已吐尽粪便,留下满腹的蛋白精华,入地蛰伏,待春化蝶了。但当不幸遇到犁头被随土翻出的时候,它便成为了我的“俘虏”。在那个肉类不怎么充足的年月,下蛰的豆虫无疑是最好的替代品了。傍晚收工回家,奶奶会把豆虫清洗干净,视数量多少,或油炸,或盐水清煮,总之,它会是爷爷的一碟不错的下酒菜。当然,我也能吃到几条,一解馋痨。
地头间歇时,爷爷会跟所有的爷爷一样给我讲一些古老的故事,但也会给我讲一些其他爷爷所没有的亲身经历的故事。其中最常讲的故事就是,他小时如何被“马子”(土匪)绑票如何被招待,家中如何卖地卖粮卖牲口托熟人找关系把他安全赎回的神奇历险。每讲及此,爷爷总不忘提到“马子”们曾招待他吃过砖头厚的大饼;另一个经常给我讲的故事就是孟良崮战役时他如何拿着两颗子弹扛着枪押送俘虏最后却一枪没放又把枪和子弹交回的略有遗憾的“出夫”经历。他说他曾要求参军,但部队上说他是独子不要他。
在爷爷不讲故事独享老旱烟时,我则喜欢仰面躺在硬硬的地上,看那鸟儿在蓝蓝的空中自由飞舞,或者期待着屁股后面“拉着烟儿”的飞机飞过。在既无鸟儿也没飞机时,我也会很好奇地侧头观看草料有规律地在老黑嘴巴与胃之间的往返与停留。在爷爷抽完一锅旱烟后,我即起身给他再续上一锅,或者用挂在烟杆上的一个铜钎子挖烟锅里那粘稠烟油子,直到烟锅子恢复它原来的铜色。或许太小的缘故,有一次我竟然在为爷爷清理烟锅时烟醉了。从此,我再也不敢碰爷爷的烟袋了,且直到现在,我对抽烟也毫无兴趣。
就这样,年华在我和爷爷的冬耕重复中逝去。我长大了,爷爷老了。冬耕的事变成了叔伯们的事。后来因到县城寄宿读书,每月只能回家一次,我就很少有时间和爷爷在一起了。但每次回家,我总会去看爷爷,爷爷也会来看我,讲一些专属我们老爷俩儿的话。
1994年的夏天,我参加了高考,并在爷爷“五七”那天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自此,我离开了村子,离开了家乡,漂居异乡,一年难有几次回。每次回乡,虽是匆匆,但我总会找时间去爷爷的坟上看看。
爷爷异界为仙已近廿年,我也近不惑,但对爷爷的思念却未曾有丝毫的减弱,有时反而更浓,特别是在秋末冬初的时候。
2012-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