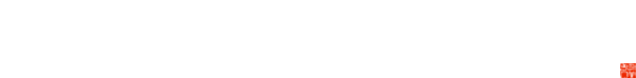采访人:王宇博,江苏教育学院历史系教授
卢新建,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级教师
编者手记:乘旦,即乘且,且即驵,古之骏马也;或意为勤勉惜时。钱乘旦,俊才也,人如其名,勤于学,敏于思,常怀为学济世之心。虽弱冠遭际文革风雨,亦未泯此志,遂于上个世纪80年代脱颖而出,成为新一代著名学者。他不仅是我国英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也是现代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本刊(《历史教学》)在酝酿“史学家访谈计划”时,钱先生是我们议论、首选的对象之一。因编辑部人力所限,我们将采访意图和提纲传达给他的学生,委托他们完成了这篇访谈录。两位采访人告诉我们,他们与先生聊了近三个小时,所谈内容使他们深受启发,相信读者们也会从中受益。
问:钱先生,当初您为什么选择世界史专业?又是怎样开始学术生涯的?
答:我从小喜欢读书,把读书当成是最大的欢乐。十六七岁的时候,我到乡下插队,繁重的劳动非常艰苦,但我觉得最痛苦的是失去了学习机会。我不甘心命运的摆布,挤出时间看书。奇妙的是,读书给了我无穷的乐趣,使我解除疲劳,消除苦恼,劳动的艰辛一扫而光。当时我看了很多马列的书,马列书中有很多对他们同时代的事件与人物的评价,我不知其所以然,就去找历史书,这样我开始接触世界历史。
1978年我考入威尼斯9499登录入口历史系,选择了世界史专业。领导把我分配给蒋孟引先生做学生,于是我就走上了学习英国史的道路。在学英国史的过程中,我对英国近代以后的发展过程特别感兴趣,并且感到英国现代化的道路很特别。我把英国史学习和寻找英国现代化道路结合起来,这样,就产生了我以后的两个主要研究方向:英国史研究和世界现代化比较研究。把这两个方向结合在一起是很特别的,至少在当时没有人做,但我起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只觉得有兴趣。
问:那么,在您的学习和学术生涯中,受谁的影响比较大呢?
答:我的老师蒋孟引先生对我帮助很大。蒋先生很有学问,是我国英国史研究的创始人,在学术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声誉很高。同时,他心胸广大,视野开阔,其学问人生,是有口皆碑的。我最初见到蒋先生时,觉得很胆怯,仿佛他是高山,我是平地。他只是很简单地对我说:“你跟我学英国史好不好?不难学。”就这样我开始了英国史学习。此后,蒋先生一步步拉着我,把我托上一个一个新台阶。我感受最深的两点是:一、他在学问上一丝不苟,认真并且严厉,对我们要求很高,一点不马虎,批评的时候很严肃,毫不留情;二、他真心实意希望学生好,希望学生超过他。每当看到我们有进步,他就喜形于色,话不多说,但充满鼓励。
蒋先生在学术上非常开明,鼓励学生标新立异,开辟新领域。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英国议会改革问题,这在当时不好做,但他鼓励我做这个课题,提出自己的观点。结果我的文章在《世界历史》上发表了。当时,这是该刊物第一次发表30岁以下作者的论文。
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我开始关注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问题,因为工人阶级在改革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由此,又延伸到现代化的模式与道路问题——英国的模式是相当有意思的。这些恰巧都是国际学术界非常关注、国内学术界又正在开始关注的领域。在现代化研究方面,我和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有很多交往,得到他很大的帮助与鼓励。罗先生的现代化研究意义很大,它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研究正在成为一个领域,因此很多人受到很大鼓舞。1987年,我的第一部著作《走向现代国家之路》(与陈意新合作)出版。在书中,我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探讨,提出“三种模式”的观点。这是当时国内第一部有关现代化研究的系统探讨的著作,因此引起较大的反响。此后,我又陆续出版了多部关于现代化研究的著作,比如《世界现代化进程》(与杨豫、陈晓律合作)、《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与刘金源合作)、《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主编)等。我还把现代化研究与英国史、欧洲史研究结合起来,先后出版《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等,并发表相关论文。
在国外学者中,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和H·T·狄金森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都是著名学者,也都是我的私人朋友。汤普森的史学思想给我很大影响,他的文化、社会史研究方法,他对工人阶级“形成”的阐述及对“阶级意识”的强调都使我深受启发。我曾把他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成中文(合译),这部书已经在中国出版。爱丁堡大学的狄金森教授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到中国来的英国历史学家,对发展我国的英国史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第一次到中国来时,感到“是到一片神秘的荒漠上来探险”,后来他和中国的英国史学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给过我很多帮助,包括为我的博士论文出版时写序言。
问:您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答:最大的困难是时间少,我们在“文化革命”中丢掉的时间太多了,不容易补回来。古人说:“人生苦短”——想做事,就觉得生命短,何况还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另外,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太“物质化”,人们不理解历史是什么、有什么“用”,不知道历史学者在干什么,为什么要研究历史,不懂得他们的辛苦与用心,这让人很伤心,是一个真正的困难。现在历史学面临“危机”,这是不正常的。一般人不理解历史学也就罢了,但如果我们的主管甚至连学术界自己都不理解,认为它无可无不可,摆摆样子罢了,那就太遗憾了。中国有深厚的史学传统,是世界上惟一能把自己的历史不间断地记录下来并不断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的国家,我们希望这个传统不会中断。
问:英国史研究是您的学术起点,因此,请您介绍一下您在英国史研究中的侧重点和主要结论。
答:英国历史内容丰富,启发性很大,从中可以借鉴很多东西。我注意到英国近代以后的历史发展是遵循和平改革的道路,不主张革命和暴力,倡导和平与渐进。我认为这是一种现代化的模式,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遵循这种模式,而英国最为典型。我和陈晓律合写的《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就是表达这个思想。我们在书中说的是:现代英国是通过改革和渐进发展来的,改革方式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的发展方式。
问:《在传统与变革之间》是您的代表作吗?
答:是的,也体现了我的代表性观点。我的观点是:英国的和平、改革之路非常值得注意,具有典型性。世界上有很多国家走过这条路,而这条路如何能够走得通,就很值得思考,因此研究英国史很有意义,从中可以得到很多借鉴。在书中,我和陈晓律教授对英国的特点进行研究。我们发现:所谓“英国的特点”,都是在对传统既继承又扬弃的过程中形成的。英国历史与其他国家的历史一样也充满斗争与冲突,但冲突与斗争的结果不像在有些国家(比如法国)那样,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一方消灭另一方,而是通过冲突与斗争达到最终融合,融合出一种新文化,产生了一个新社会。斗争中融合的方式就是英国的发展道路——和平、渐进并不意味着无斗争、无冲突;它仅仅意味着:冲突各方最终能够相互包容,形成新的社会整合体。英国现代社会就是融合而出的社会,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是在“冲突中的融合”中产生的。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属于英国的惊心动魄的场面并不多,但英国表现为沉着稳重,讲究理性,靠这些优势它率先闯进现代化的大门,成为现代世界的领路人。传统与变革在冲突中相融,是英国文化模式的特点,也是这个北海小国能够在世界近代史上成功的秘诀。
在《第一个工业化社会》这本书中,我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此外,在我和许洁明合著的《英国通史》中,我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表达了这个观点。
问:那么,您怎样看待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平、渐进的道路与工人阶级斗争是什么关系?应该怎样理解工业革命前后的英国工人运动?
答: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恰恰体现了英国发展道路的特点。英国工人阶级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也最早发动阶级斗争,但它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同,英国工人运动的主流是和平、渐进的,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应放到历史的过程中来理解。任何历史现象都不是个别人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它有其内在必然性,有它的历史条件。我的博士论文《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就是解释这个现象,寻找英国工人阶级“和平”斗争方式的客观环境与历史条件。我提出:英国工人阶级早期的斗争方式是“工人激进主义”的,它的阶级基础是正在被工业革命所消灭的手工工人。这个阶层出于其经济地位、工作方式和受剥削的形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发展出“工人激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工业革命时期的情况——一种“激进主义”运动,但它又是“工人阶级”运动。放在“工人激进主义”的视角下来观察这个时期,我们能弄懂许多我们以前疑惑不清的问题,包括宪章运动问题、“战斗性”问题等。工业革命完成后,手工工人阶层被消灭了,工厂工人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英国工人运动也从“工人激进主义”进入工会运动阶段,其“战斗性”更趋平和。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对英国工人抱有很大的期望,但结果却不是那样。相反,英国工人运动的主流始终走在渐进主义的道路上,而20世纪的“福利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这个斗争的成果。同时,“福利国家”也体现着“斗争中的融合”:资产阶级放弃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绝对性原则,而同意用有限度地重新分配私有财产的手段,来换取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与延续。有关叙述,还可在《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及《英国通史》中看到。
问:对20世纪的英国您是怎么看的?
答:在我和其他几位老师(陈晓律、陈祖州、潘兴明)合作的《日落斜阳——20世纪英国》一书中,我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20世纪的英国“衰落”了,但这种衰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从各方面说,20世纪的英国仍能跟上时代潮流,它并没有“落伍”;但它已经不能领导历史潮流。作为一个小国,英国在19世纪独霸世界是反常的,完全是因为它当时独占了工业生产力。但是当其他国家也实行工业化之后,英国“衰落”就是必然的。《20世纪英国》是一本20世纪的英国断代史,写得比较全面,愿意了解的读者可以看一看。
问:您研究的第二个方向是各国现代化进程比较,您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答:我在现代化比较方面提出了政治现代化的“三种模式”观点,即各国政治现代化过程大体上可归纳为三种“模式”:以英国为典型的和平、渐进方式;以法国为典型的革命、暴力方式;以德国为典型的旧统治者主导现代化的方式。
三种模式的特点、生成条件、表现形式及后果等等,都在《走向现代国家之路》中作了探讨。前面说过,这本书是国内较早出版的一本有关现代化研究的书,在当时很有影响。十年后,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我和我的同事对这些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并对经济发展模式也作了探讨,指出:英、法等国采用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德、日等采用的是“统制式”经济模式;苏联等采用了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等等。
在中国,现代化研究仍是一个很现实的课题,我们还有很多问题可以探讨。有人说“现代化研究”已经过时了,不必多费心。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西方早期的现代化理论确实有许多缺陷,对此人们作了很多批评和修正,但只要现代化作为一个过程在世界上仍在进行,“现代化研究”就不可避免。你可以把它叫做不同的名称(比如“发展研究”),但研究本身却总会存在。学术研究和现实需要往往不可分,现代化研究就是这样。
问:您在现代化研究方面还作了哪些工作?
答:在关于民族与民族国家方面,我提出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一切“现代化”都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发动、实行及完成的,因此,没有民族国家,就没有“现代化”。建立民族国家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头等大事,国家统一、自立、独立自主地发展是现代化的首要条件。所以你们看:一切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从解决这个问题开始。民族与民族国家问题是近来国际学术界非常热门的话题,是学术界的前沿。我提出这个观点就把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现代化问题联系起来了,可以解释为什么民族国家是必需的,必不可少。为了执行现代化的使命,民族国家是时代的需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既然是历史的需要,它就只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和其他一切历史范畴一样,它不会永恒不变。关于这个问题,可以看我的论文“欧洲民族问题的历史轨迹”。
关于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在西欧产生的问题(因为早期的现代化都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进行的),我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西欧中世纪独特的社会结构是其原因:西欧中世纪的城市和商业游离于“封建主义”主体社会结构之外,这为资本主义的生长与壮大提供了条件。这个观点比较特别,具体阐述,可以见“前资本主义社会:东方普遍性与西方特殊性”一文。
问:您与刘金源合写过《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这本书中您谈的是什么问题?
答:提起“现代化”,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种种美好的东西,似乎现代化是灵丹妙药,给人类带来最美好的前景,但这种想法是虚幻的,不切实际的。在现实中,“现代化”确实能解决不少让人类几千年来感到头疼的问题,但它也能产生很多的新问题,即所谓“现代病”,有时产生的新问题比解决的老问题还要多。现代化能给人类带来美好的前景,但也会造成很多不好的结果。而且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是失败多于成功,挫折多于顺利;成功中也会包含不成功的因素,不成功则让人不得不反省。《寰球透视》这本书研究的是“现代化的失误”,即现代化的挫折与错误,希望这些问题能引起人们的警觉,尤其是中国现在正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避免前人所犯的错误就显得更加重要。
问:您提出了“反现代化”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答:“反现代化”不是反对现代化,而是企图用“现代化”的手段来扭转现代化的方向,达到维护传统社会和传统价值观念不变的目的。“反现代化”和“现代化”方向相反,前者看起来在很多方面与后者相像,甚至好像是一样,但“反现代化”与现代化是方向相反的两个运动,前者是后者的反向操作。当现代化的潮流不可阻挡时,“反现代化”成了阻挡这股潮流而采用的“现代化”手段。一般来说,“反现代化”可以在物质的层面上进行“现代化”,但在社会目标上则完全抗拒现代化,不愿实行社会转型。这和“现代化的失误”还不是一回事,因为“失误”只是错误,它的目标还是现代化的,旨在完成现代化转型;“反现代化”的目标恰好相反,企图用“现代化”的手段来反抗现代化。因此有人建议:用“逆现代化”这个词是不是更准确一点,这个建议值得考虑。在世界现代化史上,“反现代化”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在许多国家出现过,不仅在后发展国家中存在,而且在西方先行国家中也有过,比如“开明专制”。我觉得有一个例子是很典型的“反现代化”,即中国的“洋务运动”,我有两篇文章谈这个问题,一篇是“‘反现代化’——一个理论假设”,另--篇是“再探‘反现代化’--理论构建与实例分析”。
问:我们换个话题。您对中学历史教育有何看法?
答:我感到中学历史教育的现状不尽人意。由于受应试教育的支配,在中学历史教育中历史成了死的知识,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且是背一些固定的观点,这些观点是不是站得住脚?是不是已经被新的知识推翻了?教科书都不管。历史被肢解成几条乏味的公式,没有生动的内容,只有符号,由此达到的只是可以应付考试。
有这么一个笑话,一次“文史知识大赛”有一道题:《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作者是谁?参赛者答:苏东坡。主持人拿出“标准答案”说:“错!应该是苏轼。”这件事当然很荒唐,但它表现着现在历史观念中的一种错误倾向,即把“历史”看作固定不变的,可以用“标准答案”来表达。但历史是活的知识!说它是活的,至少有两个理由,一是历史的知识不可能被穷尽,新的知识不断出现,已知的知识也可能被新的知识所取代,新的知识一出现,就应该立刻修正原有的知识,从而改变人们的观念。二是人们在观察历史时使用的角度不同,改变角度或改变方法,都会造成对历史的不同理解和不同了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标准答案”是无法表述历史的——换句话说,学历史不可把“标准答案”作为内容。
我觉得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把历史真正变活,作为活的知识,被人们教,被人们学,让历史教育的强大生命力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