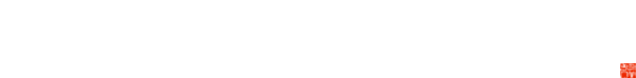一
南高史地学派因《史地学报》而得名。《史地学报》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史地研究会则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和其他科系学生的联合组织,其成员以文史地部学生为主。史地研究会的前身是成立于1919年10月1日的地学研究会。此前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研究会中,因为学校只有国文专科,而没有文史地部,故而研究会中惟独史地方面付之阙如。1919年,国文科改为文史地部,学生们就有了增设地学会的创意,此意得到了柳诒徵和地理教授童季通的大力支持,从而有了地学会之成立,共有会员67人,以龚励之为总干事。成立后,柳诒徵曾在该会做“人生地理学”等讲演。1920年1月19日,地学会换届选举,诸葛麒任总干事,会员发展为73人。5月13日开会,“初会员鉴于地学与史学,似不宜偏此忽彼”,并提交大会讨论,决定改地学会为史地研究会,通过简章。史地研究会以“研究史学、地学为宗旨”,“凡本校史学系、地学系或其他各科系同学有志研究史地者”及“本校毕业同学愿入会者”皆可成为会员;会务分讨论、演讲、调查、编辑等项;会员始终维持在近百人之间,诸葛麒、陈训慈、胡焕庸、向达等先后担任总干事;张其昀、陈训慈、缪凤林、陆维钊等人相继担任总编辑或编辑主任;柳诒徵、竺可桢、白眉初、王毓湘、朱进之、梁启超、徐则陵、陈衡哲、顾泰来、萧纯锦、曾膺联、杜景辉等担任指导员。
南高师校内的各种研究会每年都出版会刊,如哲学研究会每年出会刊2册,体育研究会每年出会刊一册,所以史地研究会成立以后就开始着手筹备会刊。史地研究会第二届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从事会刊的筹备和地质考察,但会刊并未诞生,倒是地质考察活动进行的有声有色,先后去雨花台、栖霞山、燕子矶、龙潭等地旅行考察。在胡焕庸任总干事期内,筹备刊物成了头等大事;“本会以中国史地界之沉寂,拟就力所能及,出其一得,以供社会之商榷,久蓄此意,至本届始决定”;为了慎重起见,史地研究会开了3次编辑会议,并征求指导员意见,在此基础上议决了会刊——《史地学报》的各种问题。由于准备充分,南高师出版委员会认定史地研究会会刊《史地学报》为南高师丛刊之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承印发行。校方的承认,对史地研究会会员来说实为极大之鼓励。1921年7月,《史地学报》第一期集稿完成,寄往上海商务印书馆,但商务印书馆因印刷业务繁冗,至该年11月方始出版。如此,《史地学报》真正面世是在史地研究会第四届时期。从1921年11月到1926年10月,《史地学报》共出版了4卷21期,初为季刊,自二卷二期始改为月刊(寒暑假除外);1925年三卷八期出版后,四卷一期至1926年10月方始出版,但成绝响。《史地学报》所设栏目(门类)有卷首插图、评论、通论、史地教学、研究、古书新评、读书录、杂缀、世界新闻(时事纪述、地理新材料、中外大事记)、气象报告、书报绍介、史地界消息、调查、史地家传记、谈屑、专件、选录、书报目录(书籍、杂志、论文)、会务(纪录、会员录、职员录)、通讯、史传、地志、论文摘述、表解等,但并非每期杂志均包含上述门类,而是视来稿情形而定。
除了《史地学报》以外,史地学派同人还先后办有《史学与地学》、《地理学杂志》(《方志月刊》)、《史学杂志》、《国风》、《史地杂志》等刊物。在这些刊物上,柳诒徵、竺可桢、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郑鹤声、胡焕庸、向达等人发表了大量有关史地学方面的文章,于史地之学多所措意。他们反对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浮夸和偏颇,将史地之学视为实学;主张成立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以共同进行史地研究;他们对中小学校的史地教学甚不当意,主张改善中小学校史地学的教学方法和教材,以图普及史地学。南高(东南大学)顿时成为南方的学术重镇,南高史地学派也隐为当时可与北大新文化派相抗衡的学术派别之一。本文即以南高史地学派为中心,重点探讨其为创建中国史学会所作之努力[1]。
二
傅斯年在1928年说,“历史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了一切工作的样式了”[2],从而有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中研院史语所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术机构,它团结了当时学界的一时翘楚,培养了大批后来独步中国学界的年轻后劲,努力将东方学正统争回中国,是团体研究的成功典范。
事实上,在傅斯年领导的中研院史语所成立,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之前,南高史地学派已经在倡导成立一个集合同行学者共同交流、出版学术期刊、策划并推动学术合作计划的组织、团体、研究机构。1922年,陈训慈在《史地学报》一卷二期上发表了《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一文,呼吁成立全国性的史学会。他认为,古代多有史馆,集合学者从事纂修,他们搜查编订,分工合作,已经有史学会的精神了;而西方则在16世纪后叶出现了专门的考古团体,其后不久就出现了法国古碑铭皇家学会(Royal Academy of Inscriptions and Medal)等专门学术团体,“自后史学研究,日臻发达,至十九世纪中叶,各国史学会兴起日多”。截至1908年,英国有史学会28个,法国26个,德国38个,比利时7个,而且史学会的数量与该国的史学研究水平成正比,德国数量最多,其历史研究水平也是国际领先。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史学研究,就其研究成就而言,确实德国傲视全球。返观中国,学术不振,出版界也相当沉寂,其因全在没有专门的史学团体。组织专门的史学会已经成为刻不容缓之事,它将在三方面发生重要影响:一、促进实学之研究。专门的史学会将使知识界空气由浮虚而趋于笃实,而所以说明源流,促起真实之研究者,史学会其尤要者也。二、表白中国文化。以史学会为中心,于古文化作忠实之研究,以发现完全之过去,畀中国文化以正当之地位,使外人明了中国的地位,则史学会不但有功于中国文化,且有助于世界文化。三、增加与保存史料。考古发掘事业,我国尚无人为之;且“吾国古物其有旧藏或发见者,多为外人收买,而当代之史料,又散佚无人注意,收集而保存之,实史学会之责也”。上述三端仅是举其大者而言,“至于研究史之教法,利用史学以为他学之取用,乃至间接裨助社会,其重要者尤有不可胜言者”。明乎此,史学会开展的工作将有:1、整理旧史;2、编订新书;3、探险考察;4、保存古物;5、组织图书馆博览室;6、参预近史a促进清史之编订b发行年鉴为研究资料c搜集无人注意之物,可为最近之史料。
史学会的功用和任务明确了,可是如何运作,其成员构成如何呢?陈训慈认为可以由国中各大学的史学教授和专门史家联合发起组织,然后征集志同道合的博学之士,多方筹措经费,建筑集会之所,以图渐次扩充。同时,国中有识之士也可自由组合,形成一定的研究团体,务必使我国的学术研究水平能与西方并驾齐驱,携手共进。
一年过后,陈训慈又将成立史学会的紧迫性提升到中国急需开展一场史学运动的高度,对史学会的运作也有了进一步看法。1923年,万国史学会召开,中国无代表与会,实为“邦家之奇耻巨辱”。在陈训慈看来,中国各学术中,以史学最为发达;而史学在世界各国,又以中国最为美备。西方欧美史学向来落后于中国,但近数十年来却凌驾于中国之上,究其实就是西方学者成立了学术研究团体,开展了史学运动,而史学运动的中心就是成立专门的学会。当时中国并非没有学会,如亚洲学术研究会、学术研究会、丙辰学社、尚志学会、中国地学会等,但专门的史学研究会却尚阙如。“若勉求其他从事史地研究之结合,则有北高之史地学会与南高之史地研究会;然此皆学生课余之团结,限于学校一部;审慎名义,殊未敢自侪于专门之学会。”[3]明乎此,建立专门的史学会就显得非常之急迫与重要,这就需要国内学者团结起来,以史学会为中心,共同致力于学术研究。史学会可开展之主要事业有:古史之开拓,西洋古史之再造,以及古文明之发见,多赖掘地事业之发达;旧史之全般整理;近代史料之搜集;地方史迹之保存;历史博物馆之建设;学校历史教学之统筹改造,并进谋历史常识之普及。
为了促成中国学术之发达,形成规模宏大的史学运动实为当务之急;而形成规模宏大的史学运动则以成立学会为前提,如此则“根本之图,尤当注意人才之培养”。当时中国学界专门的史地学者“自若干耆宿以外,新进中实不多觏”,而且“耆学宿儒往往与新进学者各不相谋”。为改变此种现状,陈训慈认为,此后高等院校的史地二系都应扩充增设,留学国外的也应有人专修这两科;对于有志于专攻之青年学者,更应当设法补助他们的经济,使得他们不至于为稻粮谋,可以毕生研究;长此以往,专门研究人才增多,大规模的史学运动就可以全方位展开。
陈训慈的主张可谓是南高史地学派的共同呼声。徐则陵在谈及中学历史教学的设备问题时,就认为,“一种学问之成立,必经几许研究,学术共作尤为今日当务之急”[4]。作为史地研究会的指导员,徐则陵在南高师讲授欧洲文化史和史学方法等课程,是“我国真正读通西洋史的少数人之一”[5],他也不时应邀给史地研究会会员作演讲,陈训慈等人注重学会建设,应与徐则陵有一定关系。
在陈训慈发表《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一文同时,缪凤林发表了《中国史之宣传》作为对陈文的补充。缪凤林认为当时海外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存在很多谬误,“西人虽有研究吾国历史之志愿,以文字之不同,典制之睽隔与史籍之浩如烟海,决难有成。际此以宇宙史为的之日,自我表扬,宣传吾国之历史,以答彼土之需求,因而免去种种误会,实吾史学界之天职。”要宣传国史,“非特组史学会,造就专门人才不为功”。缪凤林以为,史学会成立以后,不宜单独存在,最好附设在国内高等学校史学科中,并特设国史宣传部,挑选兼通中史和西文,并有志于终身宣传事业的年富力强的学子,在免除学杂费之外给予一定津贴,悉心培养。十年后,他们“以西文编纂翔实之国史,次及各种学术史,制度史……行销各国,或任各国大学教授,或赴各国巡回讲演,使西人了然于吾国之历史文化,不致因误会模糊而生种种恶果,国际地位,学术荣誉,两利赖之矣”。[6]可见,史学会的成立和人才的培养,有助于提高民国学者在国际学界的地位,并获得国际性的学术荣誉。但缪凤林此际主张的史学会,依然只是局限于各大高校的史学会,此意很可能是为了以后成立全国性的史学作力量上的积蓄和运作上的准备。
较陈训慈和缪凤林低一级的郑鹤声,也主张“学术研究,端赖众功”。“而今内外交通,吸收发扬,有应接不暇之势。史地疆界,日益拓广,任重道远,更非合作不为功。试观今欧西史家之言中国史者,率臆度虚测,谬误滋多。若不自起整理,则辱没国体,遗羞学术,不知伊于胡底。”[7]与缪凤林一样,郑鹤声也是基于纠正国外学者在中国史研究方面普遍存在的谬误而倡导学术研究上的合作。郑鹤声所提倡的学术合作采取什么方式呢?那就是成立史学会。他认为学术研究,本无畛域;南高师史地研究会的成立,仅是倡其先声,“深盼海内之士,分道扬镳,同怀目标,成此宏图”[8]。
揆诸当时史学界情状,成立史学会并非是仅南高师一家。在南高师史地研究会成立之前,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都成立了史地学会。北京大学历史系也在南高史地研究会成立前后筹备成立史学会,但因故中辍。朱希祖在北大史学会成立会上曾说:“我们在两年前已经发起组织史学会,办史学杂志。因为学校常有罢课的事情,欲成立而停止的已数次。”[9]在北大史学会成立之前,北大历史系学生曾发起史学读书会,该会后来成为北大史学会成立的基础。但南高师史地研究会、北高师史地学会和北大历史学会等都是局限于一校的学会组织,并未牵涉到其他高校,更遑论南北史学会之间的通力合作。但陈训慈等人谋求成立全国性史学会的创想,在当时而言是具有相当的学术前瞻性的[10]。
南高师史地研究会成立伊始,就相当重视与外界史学会的联系,以图共同促进史学发展。如北高师史地学会1920年出版会刊《史地丛刊》2期后,因种种原因停顿多时。南高史地研究会认为,“北高《史地丛刊》,自《地学杂志》外,实导史地界定期刊物之先”,对于它的停顿,深为惋惜。见到《史地丛刊》复刊后,南高史地研究会同人为之欣喜不已,并希望“异日与本报(指《史地学报》)左提右挈,以昌明吾国之史学地学”[11]。北高师史地学会对南高师史地学会甚为投契,双方互相交换会刊,“声应气求,志趣相合”[12]。
时人认为南高与北大隐然对立,互相排斥,但南高史地研究会对此并不以为意。北大史学读书会成立不久,史地学派成员就对其作了较为详尽的报道:
北京大学史学系学生张国威、王光玮等十二人,于本年四月发起组织史学读书会。其意见书略谓(1)当今史学以普遍史为归,欲各方并观,有赖于解各国文字者之助。(2)史学关系各种科学特盛,尤须专究各门者协力共进。(3)故该会目的,将以自由研究之精神,整理国史,以贡献世界。并订有简章十三条,内述其研究暂分本国史,外国史,科学史三组;其会务则为(1)读书报告(2)名人讲演(3)与外界通信研究,调查史料云云。
并认为北京大学学生自组的学术团体很多,唯独史学会久付阙如;“今有此组织,必能发扬有为。吾人对此友会,谨表示诚恳之同情与希望”[13]。因为将北大史学读书会认做“友会”,所以南高史地研究会专函与之联络,但北大史学读书会却未曾给予回应。尽管如此,南高师史地研究会还是一如既往地关注北大史学读书会的发展。当北大史学读书会发展成为北大史学会后,南高师史地学派“爰谨纪之,且以表吾人之愉快与希望”[14]。
当时中国学界南北学统间的无形对立,使得成立全国性的史学研究会成为一种不可能。大本营初期在东南大学的学衡派对北大新文化派,尤其是矛头所指的胡适等人的肆意批评和攻击,初显南北学派之间的差异。史地学派在反对新文化运动过激行为,弘扬传统文化上,与学衡派达成共识。他们还与北大后劲顾颉刚倡导的疑古运动发生了论战,双方你来我往,激战于先秦古史问题。虽然最终结果,双方都未曾有足够的理由说服对方,但就社会反响和支持力量而言,在表层上,古史辨一方获得了胜利。从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对胡适治学的批评,到史地学派与古史辨派的论战,无不说明了南北学界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和对立。按照胡适的说法,就是南北治学精神存在差异。南北两方面的学风存在很大差异,“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信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15]就大致情况而言,当时南北学风差异确实如此。此种差异反映到学校之间,就无形中形成了南高(东南大学)与北京大学之间的对立[16]。当时南高史地研究会致函北大史学读书会,试图联络感情而无回应,就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北方学界以正统自居,对南方学人的学术活动不甚在意的一种心态[17]。此种情状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界因素的影响等原因,南北史学界联合而组建成全国性的史学会只能是一种空想。
三
1925年,东南大学发生了“易长风潮”。教育部免去郭秉文东南大学校长职务,改任胡敦复为校长,引起了部分师生的不满。柳诒徵牵涉其中,处境尴尬,最终愤而出走东北大学,与先他而至的缪凤林和景昌极等人会合。此时,竺可桢也因不满东大部分师生对部聘校长胡敦复的过激做法,而应商务印书馆之聘;梁启超在1923年就离开了东南大学;杜景辉也在1923年11月病逝;陈衡哲留宁半年后回到四川;徐则陵担任历史系主任不久,就转而主持教育系;顾泰来在东南大学任教不久,就远走北京供职外交部;白眉初也在南高师任教不久,回到北京高师。绝大部分指导员的离去,使得史地研究会会员无从请教治学津梁;其中又以柳诒徵和竺可桢的离去损失最大,因为平时史地研究会开展的具体活动和学术论文的撰写都是由他们二人负责。1923年,胡焕庸、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和诸葛麒等人的离校,意味着史地研究会骨干新陈代谢的开始;1925年,向达、郑鹤声、刘掞藜、陆维钊等人的毕业离校,更是史地研究会核心成员的风流云散。后继的史地研究会成员中,很可能缺少上述诸人的才干,虽然陈登原曾经主持过史地研究会,但仅凭一人之力,实在是回天乏术。因东大“易长风潮”影响,《史地学报》3卷8期延至1925年10月出版,而其终刊号4卷1期,更是拖至1926年10月方才问世,其间间隔长达一年,可以想见当时史地研究会人才之匮乏。
虽然当时史地学派成员星散各处,但他们并未放弃成立全国性史学会的努力。柳诒徵认为,“欲明宇宙之真相,舍治史地,其道无由”,“欲知国家之真谛,舍治史地,其道无由”,“欲识人生之真义,舍治史地,其道无由”[18]。与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向达等人商议成立中国史地学会事宜,在诸生支持的情况下,成立了中国史地学会,发刊《史学与地学》杂志。中国史地学会会刊《史学与地学》并未刊载有关该会的详细情形,仅就目前所知,成员依然为南高师时之师友,柳诒徵担任总干事,具体的编辑和问题商榷等事项由任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向达和张其昀负责。从《史学与地学》刊发文章来看,也以史地研究会同人为主。所以,我们可以认定柳诒徵等人组建的中国史地学会虽然以“中国”为号,但他其实是南方学者,或者说是南高学人的一个自发组织,地域限于江浙一带,成员也为南高师旧人,故而完全是一个地方性组织。
1928年,胡焕庸留法归来,任教中央大学,并和张其昀一起创办了《地理杂志》。本来《史学与地学》将历史学和地理学都囊括其中,现在张其昀等人另创《地理杂志》,并与缪凤林、陈训慈、范希曾、郑鹤声等人倡议另创《史学杂志》以呼应之。“盖孪生之子自毁齿而象勺,虽同几席而各专其简策之通轨也”[19]。既然犹如孪生兄弟的史学与地学已经分家,中国史地学会之名就有点名实不符了。经过酝酿,1929年1月,南京中国史学会成立,并于同年3月创刊《史学杂志》。无独有偶,北方的朱希祖等人也与柳诒徵等人差不多同时组建中国史学会。1929年1月7日,朱希祖作《发起中国史学会的动机和希望》一文,表达了自己发起中国史学会的三种动机和七种希望。1929年1月10日,朱希祖与张星烺、罗家伦共拟中国史学会简章。1929年1月13日,“中国史学会开成立会,到会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六校教授、学生共九十四人,推公为主席,并以七十四票,当选为首席委员(其次为陈垣六十票,罗家伦四十九票,钱玄同四十三票,王桐龄四十一票,张星烺三十九票,沈兼士三十三票,陈衡哲三十一票,马衡三十票,候补者陶孟和、袁同礼、萧一山、刘崇鋐、翁文灏五人)”[20]。1929年1月20日,开中国史学会第一次委员会,朱希祖当选为主席及征审部主任。
南北学界同时出现中国史学会,说明史学界对于协作治史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在理论上为成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史学会打下了基础。但南北两方的中国史学会均无多大建树,未能使对方心悦诚服。南京中国史学会与南高史地研究会和中国史地学会一脉相承,研究旨趣和成员大体上相对固定。《史学杂志》以“发表研究著作,讨论实际教学,记述史界消息,介绍出版史籍”为宗旨,对国际史学界的动向依旧给予很大关注。1928年8月,国际历史学会第六次大会在挪威首都奥斯洛举行,陈训慈在1929年3月出版的《史学杂志》创刊号上作为史学界消息加以报道,然后在1929年5月出版的《史学杂志》第1卷第2期上专门从美国《史学杂志》译载了《国际历史学会第六次大会记》,认为“此次盛会,中国虽未有代表参与;然史学研究之国际合作近况,与各国研究之趋势,当为国内研治史学者所注意……吾人以中国人之地位而言,尤望国内学术界得循政治之渐趋安定,而有健实之进步,届时国内史学界再不致如此次之漠视此会,而能由学术团体与政府之合作,推定代表前往参与也”。此外,南京中国史学会还出版了《南京中国史学会丛书》,计有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唐宋元市舶史料》、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和《日本论丛》、陈鼎忠的《通史叙例》和《六艺后论》等。在刊布同人著作的同时,希望能扩大南京中国史学会的影响。而北京的中国史学会在具体事业规划上较南京中国史学会详明,但这些活动最终都没有切实有效地进行[21]。北京方面中国史学会的成立和所拟开展的具体事项,说明身在中国学界主流圈子的学人开始有意识地借鉴国际史学会模式来建设中国史学。就此认识而言,北方学人明显滞后于以柳诒徵等人为核心的南高史地学派;而柳诒徵等人在成立中国史学会之际,前冠以“南京”二字加以限定,很显然从前此之中国史地学会的运作中认识到,南北史学界存在很大差异,在短时期内很难沟通,所以自囿于“南京”一地。
尽管中国史学会事不可为,但在地方性的史地学团体建设方面,陈训慈等人开展得有声有色。1936年1月12日,陈训慈等在浙江省立图书馆举行了浙江中华史地学会成立大会,以研究史地,阐扬民族精神为宗旨。会议选举陈训慈、李絜非等9人为理事,刘文翮、蒋君章等五人为候补理事。同年12月27日举行本届年会,并决定改名为浙江史地学会,会议选举张其昀、陈训慈、董世祯等9人为理事。抗日战争爆发后停止活动。在浙江中华史地学会开始运作时,另外一个地方性史地学团体——吴越史地研究会,也于1936年2月,由一部分热心研究江浙古文化的学者在上海发起,李济、柳诒徵、朱希祖、缪凤林、董作宾等人参与了发起注意事项的讨论。1936年8月30日下午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行成立大会,与会者有宁、沪、杭等地会员60余人,蔡元培任大会主席。大会通过的《简章》规定:“本会以研究吴越(暂以江苏、浙江两省为限)史地为宗旨”,“凡有志研究吴越史地者得申请入会……”,“本会设于上海,并得于江苏、浙江两省设立分会”[22]。大会推举蔡元培为会长,吴稚晖、钮永建为副会长,卫聚贤为总干事,马衡、柳诒徵、何炳松、李济、陈训慈等任评议,朱希祖、吕思勉、缪凤林和张其昀等人任理事,董作宾等为常务理事。
虽然南高学人参与、发起了一些地方性史学团体,并徐图扩大至全国;北方的清华大学历史学会、燕京大学历史学会、北平研究院历史学会等也都开展了不少工作;但于中国史学会的建设却有无从着力之感。1933年在华沙召开的国际历史学会第7次大会,中国史学界却依旧无人与会。位居中国史学主流的北京学术团体,尤其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机关未曾派人参加,说明傅斯年等学人在中国史学会建设问题上所给予关注程度不够[23]。当时中外史学交流比较频繁,一些中国学人如王国维和陈垣等人都取得了很高的国际声望。对于史学大国未曾参与,国际历史学会也颇为注意。1936年底,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应上海各大教授会常委康选宜邀请来华。“康氏以中国至今无历史学会之成立,对于史学之研究亦不甚注意,故特约田氏来华讲学,以提高国人对史学之注意,并促进中国历史学会之成立。康氏抵平后,与平方历史学者研讨结果,认为确有从速组织中国历史学会之必要,并决定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姚士鳌先生及清华大学历史系刘主任负责在平联络发起;中央大学罗校长负责在京联络发起;上海方面则由康氏南返后进行,务期赶速成立,并希望派代表出席一九三八年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历史学大会。”[24]该消息说北京方面由姚士鳌和所谓的刘主任负责等,未提及顾颉刚,可能初始商议结果如此,因为登载此则消息的出版日期为1936年12月10日,可能未及当时最近的发展动态;但后来的相关筹备运作事项均与顾颉刚发生了莫大关联。1936年12月1日,顾颉刚与陶希圣、连士升一起到北京饭店拜访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商议组织中国历史学会以便加入国际历史学会事项[25]。具体讨论问题主要有中国入会问题、入会后中国政府之援助与中国的财政担负和中国历史学者即时开始史学工作之条项等。次日,田波烈致函顾颉刚,请他协助进行此事。在田波烈给顾颉刚的信中,田氏表示“我愿意并且希望你能领袖着把它组织起来”,“我也相信没有人比你更有资格来辅助这件伟大的工作”[26]。同时还附上“中国历史学者订购公报减价通告”,因为按照规定,每个与会国或会员国均须订购国际历史学会年出4期,年价75法郎的《世界历史学会公报》。
在确认田波烈会努力帮助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后,顾颉刚与郑振铎、罗家伦等人开始积极筹组中华史学会,作为中国研究历史的最高研究团体。经过各方交换意见,彼此都认为此事极为重要,决定将中华史学会总会设在北京,上海、南京和广州等地设立分会[27]。但由于时局变换过快,抗战军兴,筹组中华史学会一事很可能就此作罢。顾颉刚在1937年7月21日的日记中如是写道:“予在平所管事,燕大史系主任交煨莲或贝庐思女士,禹贡学会交宾四与张维华、赵肖甫,歌谣学会与方纪生等,通俗读物社则移绥办理,只剩一北平研究院,仍可遥领也。”[28]在顾颉刚的工作安排中并无只字提及中华史学会,可见此事已经淡出了顾颉刚的视线。不过,虽然顾颉刚等人组建中华史学会并未成功,但胡适还是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1938年在瑞士召开的国际历史学会第7次大会,并宣读了论文。中国也在此次会上,与爱尔兰和梵蒂冈史学会一起成为新的会员国[29]。
田波烈来华虽未能真正促成中国史学会的诞生,但在很大程度上让中国史学界学人明白了努力方向。随着抗战爆发,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南北学人终于开始逐渐摒弃前嫌,不再过分主张双方在精神方面的不一致[30],开始了合作。1940年4月,民国教育部成立史地教育委员会。吴俊生、张西堂、黎东方为专任委员,陈东原任秘书,吴俊生、颜树森、陈礼江、张廷休等7人为当然委员,吴稚辉、张其昀、蒋廷黻、顾颉刚、钱穆、陈寅恪、黎东方、傅斯年、胡焕庸、徐炳昶、雷海宗等19人为聘任委员[31],柳诒徵、陈训慈、郑鹤声也是史地教育委员会成员[32]。该会于1940年5月14日举行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了“改进大中小学史地教育事项、推动社会史地教育事项、编纂中国史地书籍事项、编制抗战史料事项”等议案[33]。1941年7月4日至6日,史地教育委员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顾颉刚和缪凤林、金毓黻、黎东方一起提出《由本会补助设立中国史学会案》[34]。该议案获得大会通过,决定将史地教育委员会作为筹备中国史学会的通讯处,并由该会酌助经费及发函征求专家学者意见。到了1942年,已经征得116位专家同意,地点遍及后方各省。鉴于此,史地教育委员会决定另案呈请准予定期开成立大会,拟与史地教育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同时举行[35]。1943年3月24日,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大会召开;与此同时,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也在中央图书馆举行,顾颉刚、傅斯年、方豪、雷海宗、缪凤林、陈训慈、张其昀、郑鹤声、卫聚贤、吴其昌等120余人到会。顾颉刚担任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大会通过了《中国史学会会章》,选举了理事和监事,其中理事21人,内有柳诒徵、缪凤林、张其昀、陈训慈等史地学派成员。1943年3月26日,中国史学会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召开,顾颉刚、傅斯年、朱希祖、缪凤林和陈训慈等9人被选为常务理事。至此,中国出现了形式上统一的中国史学会,南北学人也于一定程度上统一于中国史学会之内。“但总的来说,该会没有太大的作为,与其创办之宗旨并不相称。战后复员,学人星散,中国很快又陷入新一轮战乱。随着政治动荡和经济崩溃,学人不得不为生存与生计奔波,无暇顾及学术研究和学术团体的活动。”[36]
可见,终民国之世,南高史地学派成员都在孜孜追求着成立统一的全国性史学会的愿望。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仅具先声”,到中国史地学会,到南京中国史学会,到中国地理学会,到吴越史地研究会,到浙江中华史地学会,乃至到抗战时期的中国史学会,无不留下了他们努力的足迹。他们创建中国史学会的努力,不仅有理论的指导,也有不懈的实践。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史学会的成立,但其中过程之曲折,则又彰显了民国时期南北史学界之间存在的对立情绪。正是此种情绪的存在,严重延缓了统一的中国史学会出现的进程。
注释:
[1]桑兵教授近在《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上刊有《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会》一文,论述了当时存在的一些地方性史学会和新旧中国史学会,也曾涉及南高史地学派;但本文以南高史地学派为中心,重点探讨他们对创建中国史学会所作之努力,视角与桑兵教授有所不同。
[2]岳玉玺等编选:《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4页。
[3] 《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史地学报》2卷3期。
[4]徐则陵:《历史教学之设备问题及其解决之方法》,《史地学报》1卷3期。
[5]张朋园等:《郭廷以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第119页。
[6]缪凤林:《中国史之宣传》,《史地学报》1卷2期。
[7]郑鹤声:《清儒之史地学说与其事业》,《史地学报》2卷8期。
[8]郑鹤声:《对于史地学会之希望》,《史地学报》2卷5期。
[9] 《朱逷先教授在北大史学会成立会的演说》,《北京大学日刊》第1116号,1922年11月14日。
[10]燕京大学历史学会于1929年成立后,曾对自己提了三点希望。其中一条就是“从今后当体学术无畛域之真谛,联络各校同好,共谋中国史学会之发展,共同工作,以发扬史学,整理国史”。此点希望与郑鹤声所提之愿望类似,但困于多种因素,希望终究是美好的希望,并未水到渠成地成为现实。
[11] 《北京高师史地学会近讯》,《史地学报》1卷4期。
[12] 《北高史地学会近讯》,《史地学报》2卷2期。
[13] 《北京大学史学读书会》,《史地学报》1卷4期。
[14] 《北京大学史学会成立》,《史地学报》2卷3期。
[15] 《胡适日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438页
[16] 南高与北大之间的对立,学者多片言只语提及。如张其昀在《吾师柳翼谋先生》一文中说:“民国八年以后,新文化运动风靡一时,而以南京高等师范为中心的学者们,却能毅然以继承中